藏在記憶裡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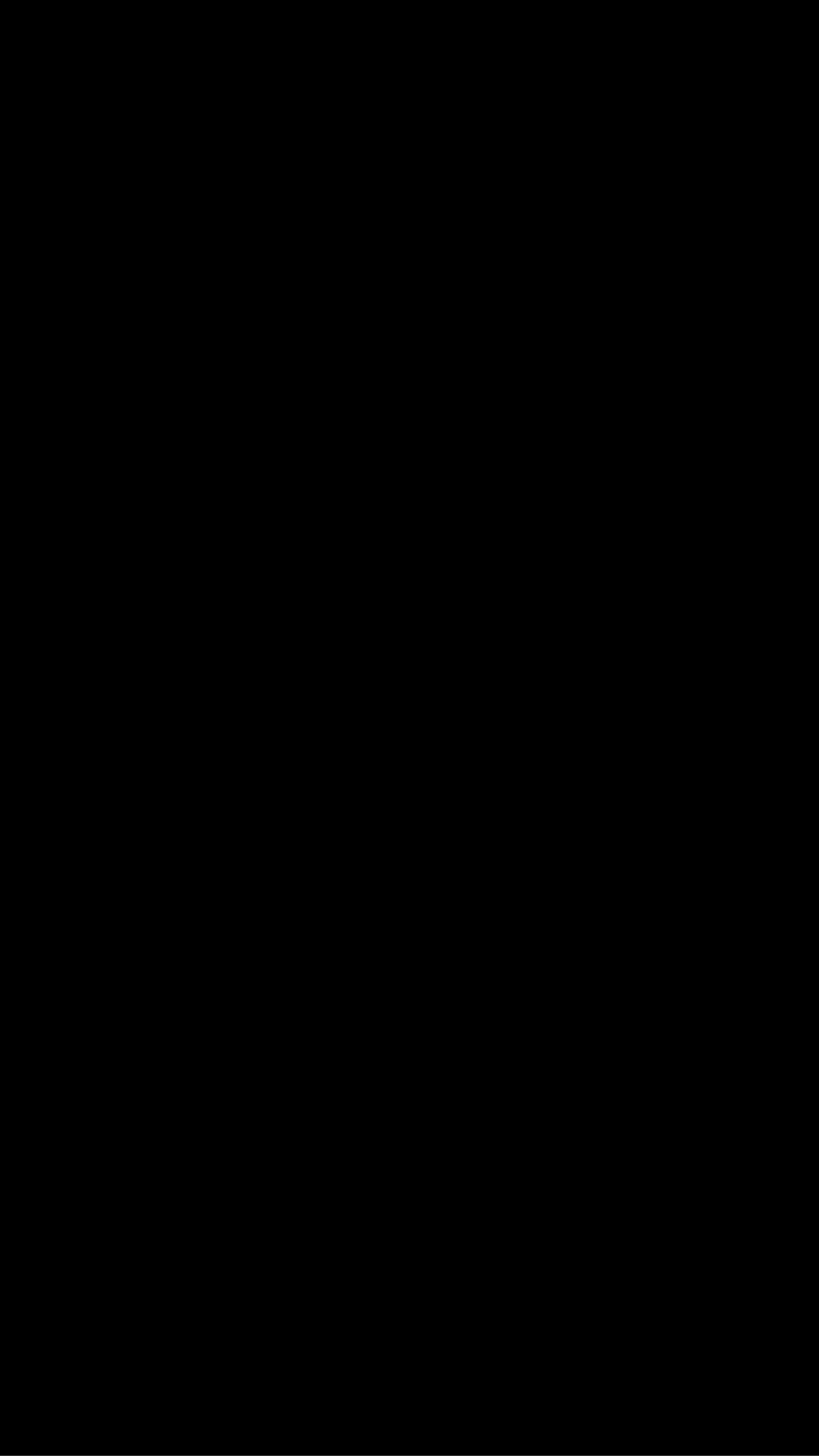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11日
- 讀畢需時 13 分鐘
Summary:宮侑改不掉那些他已化作肌肉的習慣。
今年是宮侑到國外打球的第三年。
日子數著數著,轉眼間也在法國落地了兩年多,那些初來乍到以為不會有起色的糟糕經歷,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逐漸有了好轉的跡象。
鎖好門,離開公寓之後,宮侑走到街道轉角處的攤販,按照慣例點了一份鮪魚總匯三明治與一杯熱可可,儘管還帶著生澀的口音,但他講得磕磕絆絆的法語終於也流利到不會點了A餐卻送上B餐,宮侑仍記得某次跟隊友聚餐時,服務生端上的某種淋上怪異白醬的生澀肉類,嚐起來的味道可真是糟糕透頂,回想起來他吐了吐舌,忍不住又想回去再多刷幾次牙。
接過剛做好的餐點,宮侑轉了個彎,在那一條他已經走過幾百遍的小徑拖沓著步伐,朝市區的方向前進。熟悉幾條日常生活的必經路線,也學會在地人的小技巧後,他總算撐到目前第五個月了,都沒有再換過一個新皮夾,那群小朋友再也沒有機會在他為大衣沾上冰淇淋而手足無措的時候,趁機扒走他的錢包,真是一群調皮到他想直接把他們種進花圃裡的小兔崽子。
宮侑也趁著非賽季的日子到一些更為偏遠的地區走踏過,上次在酒莊買回來的葡萄酒,現在打開來風味應該不錯吧?等一下繞到附近的超市買一些下酒菜回來好了,烤牛肉是個不錯的選擇,他會的料理不多,這大概是他所能想到最不會失敗的一項料理。
宮侑邊信步走在街道上邊思索著,嘴裡的吐司吞下去了,他便又慢吞吞地咬了一口三明治,配上一口可可潤喉,腳下的板鞋踩在滿地的銀杏上沙沙作響,這陣子沒有比賽,除了早上既定的練習菜單,剩下的時間皆由他們自由安排,也因此下午時分他才能夠如此悠閒地走在大街上,享受溫煦的陽光,無憂無慮,只需要為下一餐煩惱。
手機突然傳來叮咚一聲,宮侑掏出手機,打算懶洋洋地瞥了一眼是誰傳來的訊息就收回口袋,手指卻先不小心按到,於是螢幕切換到家庭群組,一張好幾尾鮮美的秋刀魚躺在碎冰上的照片頓時映入眼簾,母親說她正在市集挑秋刀魚,要宮治回家一趟聚個餐,還標記了他好幾次,要他就算開店忙,也不要連私人訊息都不看,瞧見宮侑立刻已讀訊息之後,母親也連帶標記了他,問他在法國最近過得如何,最近傳到群組分享的照片越來越少了。
但我的生活就那樣嘛,打球、吃飯、訓練,怎麼拍都一樣。宮侑當即回覆,又按了一張無奈狐狸的貼圖,想要發些什麼圖片回報,卻發現相簿裡的圖還停留在上週午餐的沙拉照,於是他只好抬頭張望了會兒,走進附近的公園,擇了一處背景的建築物還算順眼的地方,拍了一張銀杏盛放的風景照當作本週的家庭群組作業,見母親回傳了一張充滿著愛心與飛吻的貼圖,宮侑才收起手機,在不遠處的長椅坐了下來。
此時深秋時節,最是銀杏金黃之時,宮侑的住處附近開滿了一片亮燦燦的銀杏,這是他先前在日本不曾有過的體驗,兵庫縣最多的還是楓葉樹,每逢秋季來臨,從住家到稻荷崎的校門口是兩排連綿不斷的楓葉,人行道上鋪滿了橘紅的掌形葉片,陽光自間隙灑落,輕盈柔軟地沿著葉緣綴著光芒,映在眼裡的暖橘因光斑而模糊了幾分,或許也有受到睡意的影響,宮侑不得不承認,畢竟楓葉盛開時總撞上他們的期中考試,熬夜趕作業跟念書是常態,早上的晨練更是一場兵荒馬亂。
比起法國銀杏的金黃,或是日本楓葉的火紅,在他的記憶裡,除了那些念不完的書與掛在及格邊緣的考卷,每個早晨倒在宮治的肩膀上呼呼大睡而流下的口水更代表了秋季。
「喂死豬起床,到學校了!」
「什、什麼⋯⋯」
「我的肩膀都濕掉噁心死了,下次你去靠窗睡。」
「哪有!我都沒有計較你剛才靠在我頭上睡到磨牙欸蠢豬!」
「誰磨牙了!」
手機再度傳來叮咚兩聲,這次宮侑沒有誤點,而是拉下通知欄預覽,還是來自家庭群組的訊息,這回輪到宮治回覆,他只傳了一句簡單的「到外縣市去了,要下禮拜才回的了家」,沒有表情符號,也沒有貼圖,預覽的縮圖裡還能看見母親拍的秋刀魚。
哎,真是可惜了那幾隻看起來這麼好吃的秋刀魚。宮侑腹誹。
秋季吃秋刀魚一直是他們家的習慣,這一點直到兩兄弟到外地發展了也從未改變,於是碰上賽季回不了家的折衷辦法便是改成在飯糰宮延續傳統,宮治負責烹調秋刀魚,俐落地在魚的表面畫上幾刀後,雙面抹上鹽巴,再撒上些許調味後即能送入烤箱,宮侑則負責將檸檬切半,等著在秋刀魚上桌時,將現擠的檸檬汁均勻地淋在表面上。
「你好歹也學一下怎麼烤秋刀魚吧?很簡單啊。」
「不用吧?反正你會弄就好了啊,切檸檬這種重責大任就交給我。」
「⋯⋯怎麼這麼大了還懶得跟豬一樣。」
「蛤我都沒有嫌棄怎麼會有這麼小氣的老闆了!」
「好好好我最小氣,秋刀魚烤好了,快去擠你的檸檬宮選手。」
可惜了,他當初真的應該要好好聽阿治的話,才不會懷念起家鄉味時一點辦法也沒有。宮侑嚥下最後一口三明治,鮮嫩的鮪魚在嘴中化開,滋味嚐起來卻有幾分秋刀魚的香氣。
他不是沒有嘗試過自己烤秋刀魚,甚至可以說是很多次,明明材料相當簡單,只需要準備鹽巴、黑胡椒粒、胡椒粉、橄欖油與檸檬,偶有幾次宮侑也曾到廚房看宮治操作過,但無論他怎麼試、怎麼更改配方的比例,烤出來的秋刀魚都不是舌尖上熟悉的味道,久而久之他便也放棄了,選擇將這份習慣與思念置之不理,如今卻因母親的那張照片,才又讓他回想起來,而大抵是因彈性疲乏,亦或是太久沒回家終於思鄉成疾,那些過往隨著秋刀魚排山倒海般蜂擁而出,一一出現在他眼前。
有太多太多了,關於秋天的回憶與習慣,早晨固定沾在宮治制服上的口水、夾在作業簿裡的楓葉葉片、烤箱裡散發出香味的秋刀魚與專屬於他的特製烤飯糰、飯糰宮門口前的糖炒栗子攤位、混雜著柚子酒的酸甜親吻⋯⋯那些昨日的碎片彷彿化作他身上的肌肉,宮侑改不掉這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每一個習慣都是胸腔裡的一根肋骨,這根代表著賞楓季時他與宮治總愛買的那間和菓子店的限定糕點,那根則是宮治津津有味地吃著秋刀魚的模樣,他們一根根井然有序地排列,左右對稱得像是一對雙胞胎,年復一年,肌肉隨著時間與記憶攀附長出,每逢季節變換之際,不同的區塊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隱隱作痛。
忙碌時宮侑還能裝作無所謂,痛起來時卻連一滴眼淚也掉不下來,胸脯明明堵得心慌,像是下雨前包裹住全身的空氣,既濕悶又黏膩,氧氣宛若全被水氣取代,大片的烏雲籠罩住天空,晦暗的灰填補住每一隅陽光灑落的所在,像是看不見放晴似的,整座城市自他離開日本以後,始終都維持著同一副樣貌。
沒有傾盆如注的暴雨,也並非終年寒冬的冰天雪地,宮侑的城市仍正常運轉,只是少了一些什麼,明知道只要下一場滂薄大雨就能趕走無盡的陰暗,他卻遲遲等不到那場遲來的雨,於是宮侑終究只得讓想念潰爛成災,在胸口逐漸腐蝕,然後堆起沒心沒肺的笑容,拍下嶄新的相片,設法建立新的習慣與生活來掩飾一切。
宮侑不曉得要怎麼忘卻那些鐫刻入骨的記憶,是不是只要剮掉連接著骨頭的肉塊,抽乾連結彼此的血液,刨去一樣的面龐,改掉那曾經讓他引以為傲卻又難以直視的姓氏,他與宮治就真的是相異的兩個個體?可以拾獲自由、可以毫不畏懼地相愛,可以在鴿子飛過的廣場前親開彼此的嘴唇,可以理所當然地吻去對方嘴角的米粒。
可是怎麼辦?那些早就已經是他的一部分了,他的骨頭他的血液他的面容他的姓氏,如同DNA的序列,早已改變不了了。
手裡的紙杯握在手中捏出皺摺,倏地一顆黃藍相間的排球滾到腳邊,打斷他的思緒,宮侑拾起排球,雙手自然而然地轉了幾圈,直到面前有一雙小手揮舞,他這才發現一個約莫五歲的法國小男孩站在他面前,視線直盯著排球,眼巴巴地眨動著靈動的雙眼。
「啊抱歉抱歉,這是你的球嗎?」宮侑從長椅上起身,將排球遞還給他。
「嗯是我的,謝謝大哥哥⋯⋯」
宮侑對他露出一個淺笑後坐回長椅上,但過了半晌,男孩仍抱著排球駐足在原地,圓滾滾的眼睛隱身在排球後面,眨呀眨地注視著他。
察覺到這熱烈得不容忽視的視線,宮侑無奈地放下熱可可,起身走到他面前,彎下腰來直視他。
「小朋友,你喜歡打排球嗎?」
小男孩睜大著一雙清澈的藍眼睛,毫不猶豫地重重點了幾下頭,嗓音瞬間拉高了幾分,「喜歡!我都會去現場看排球比賽唷!」
「哦,這麼大聲真不錯!」宮侑摸了摸小男孩的頭,他忽然靈光乍現,便又問道:「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小男孩頓了頓,過了一會兒才說道:「嗯⋯⋯大哥哥是誰啊?不知道耶。」
宮侑鼻腔淺淺哼了一聲,無奈地搔了搔自己的脖子。
哎也是,就算在日本他已經代表國家隊對外征戰了,放在國外,雖然也累積了一些戰績,但果然還只是一個不備受矚目的舉球員。
「大哥哥是舉球員喔,很厲害的那種!」
「是嗎?那我怎麼會不知道?真的很厲害嗎?」男孩眨了幾下眼睛,神情看來相當無辜。
宮侑聞言結舌,一時答不上話,現在的小朋友還真不可愛,他拿起熱可可啜飲了口,猶豫著是不是應該要轉身就走,但倘若現在離開,離晚餐時間還有一段時間,宮侑在心底嘆了口氣,決定再給小男孩一次機會,便隨口拉開話題。
「哦你知道舉球員啊?那有想過以後要打哪一個位置嗎?」
「我覺得主攻手很帥氣!但我哥哥說裡面最帥的當然是舉球員,是組織進攻的司令塔,所有的攻手能否進攻都靠舉球員的判斷。」
宮侑點頭如搗蒜,孩子終於吐出一句像樣的話,果然朽木還是有辦法雕琢的,「你哥哥說的真的很對,啊對了,你的家人呢?」
「喔⋯⋯我跟哥哥來公園練球,但他說他要去買巷口的糖炒栗子,然後就不見了。」
「啊我懂我懂,我也有這種會因為食物就忽然消失不見的兄弟,真的很困擾對吧?」
「對啊對啊,我們明明練球還練不到十分鐘⋯⋯」小男孩不滿地嘟囔道,嘴巴翹得老高,卻在看向某處時表情忽然變得歡喜,眉眼一片柔和,「我看到哥哥了!啊⋯⋯他怎麼買了一大最大包的,是豬嗎?」
宮侑隨著他的視線回過頭去,只見一個長相與小男孩幾乎一模一樣的小小身影正蹦蹦跳跳地在公遠裡來回張望,他的手則馬不停蹄地撥栗子,從撥開到丟進嘴裡,動作一氣呵成,那姿態與宮侑記憶裡某個角落的人影重合。
一夕之間,彷彿又回到了那個楓紅色的秋天,他抱著一大袋糖炒栗子,他罵他是不是豬,兩人坐在公園裡的長椅上,圍著那一袋香氣撲鼻的栗子大啖起來。
「你們是雙胞胎嗎?」宮侑低聲問道,聲音不自覺暗啞了幾分。
「嗯嗯對呀,天啊他要把栗子全都吃完了吧?怎麼連我在這裡都沒看到好笨,我要去找他了!」小男孩抱著排球,往手足的方向跑去,跑到一半他似乎想起什麼,因而轉過身雀躍地揮舞著手,「宮侑選手再見~」
「掰掰!欸等等,什、什麼?這不是明明就有認出來嗎⋯⋯」宮侑望著小男孩的背影無奈地笑了笑,他看見那兩個小小的身影重聚之後拉扯了好一陣,模模糊糊的,他看不清楚那究竟是打架還是擁抱,唯一能確定的是他看見他們牽起手,一同往街道奔去,直到兩人雙雙隱沒在街角之後,宮侑才移開目光,回到眼前杳無人煙的銀杏大道上。
金風細細吹拂,摩挲過銀杏擦出颯颯的聲響,國外的秋天真是冷得不尋常,宮侑下意識縮了縮脖子,纏緊圍巾,但冷冽的寒風依然鑽進他的袖口,順著縫隙拂過胸口,若有似無地擦過左胸的第二根肋骨處。
宮侑捏緊手中冷掉的熱可可,一口氣飲盡後將紙杯扔進公園出口處的垃圾桶,微涼的苦澀還殘留在他的舌尖打轉。
「啊⋯⋯好苦喔,都冷掉了⋯⋯」
「這種時候最適合來一個甜甜圈了。」
「還是沾滿糖粉的那種!」
「哪用你說?那是最基本的吧!」
熟悉又遙遠的聲音在腦袋裡驀地響起,過去的他們也是這樣,喜歡在秋冬之際到便利超商去,用最便宜的價格,一人捧著一杯冒著熱氣的熱可可慢吞吞地走出來,他們雙手緊緊握住杯身,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飲,就算熱可可涼了也捨不得放手,努力汲取零星的餘溫,走在回家或是上學的路上,肩併著肩,偶爾仰望天空,偶爾盯著腳上被踩髒的鞋帶,說著不著邊際的話。
於是一杯冷掉的熱可可、一個夢想中得以中和苦味卻從未實現過的甜甜圈,布丁、米飯,以及一切美好與不美好的事物,建構了他們相攜的歲月。
哎,怎麼老是想起這些早就應該要忘記的瑣碎回憶⋯⋯
宮侑感慨地想著,嘴角掛著自嘲的笑容,他不是記性多好的人,更多時候總是會被父母或老師責備過於健忘,他倒也不以為意,因為大多都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再不然宮治也會替他記著,提醒他記得帶隔天要交的作業、叮嚀他填寫報名賽的表格、囑咐他搬進黑狼宿舍要帶哪些東西才不會麻煩到別人⋯⋯有太多太多了,宮侑這才驚覺,就連當時他搭飛機來法國的前一天晚上,都能收到自家兄弟的簡訊,提醒他要記得提前幾個小時到機場,以免弄錯流程而錯過航班。
當初宮侑只是嗤之以鼻地哼了一聲,心裡一邊想著怎麼可能會忘記呢豬頭,手指一邊移到刪除鍵上方。
畢竟他們實在不能算是好聚好散,一時的賭氣、一時的衝動,那些實際上的原因跟對外宣佈的藉口,如今回想起來,宮侑也無法說清離開的理由,或許他又忘了,只記得一眨眼他就飛越重洋,佇立在法國的機場,等待行李運輸到手上;只記得一眨眼那封簡訊至今還停留在他信箱的最底部,從未刪除。
也許是宮侑僅存的記憶體都讓給了那些過於重要且顯眼的存在,所以一旦撥開那建構出他夢想的黃藍色球體,才會怎麼翻、怎麼尋,都只看得見宮治。
那是比排球還要更早以前,就深植在整個宇宙裡的色彩。
當宮侑越過轉角時,前方忽然出現一輛以前不曾出現過的甜甜圈餐車,老闆正將炸鍋裡的一個個炸得金黃酥脆的甜甜圈起鍋,那並非他在日本常吃到的,中間挖洞的甜甜圈,而是當地的傳統造型,似方卻又有些扭曲,裹滿糖粉的道地法式甜甜圈。
宮侑一時怔住,彷彿聽見他的心聲似的,眼前竟然真的出現一間甜甜圈的小攤販。
「午安,要來一份甜甜圈嗎?」老闆熟練地將甜圈圈裹上糖粉,眼角含笑地對宮侑說道。
「請給我一份。」宮侑從大衣的內袋裡掏出錢包,零錢剛數到一半,他才驀地想起今天似乎吃得有些超過,回去可不又要被營養師碎念一番,糾結了半晌,他歪著嘴巴,心不甘情不願地說道:「老闆,不用幫我灑糖粉,謝謝。」
「老闆,那可以把他的那一份糖粉加到我這裡嗎?我也想要一份甜甜圈。」
「沒問題!」
如內化成生理反應,宮侑聞聲旋過身,聲音的主人映入眼簾,他烏黑的髮絲還是一如往常乖順地貼在額前,整身衣著也如往昔以素色為主,唯一改變的似乎只有身材,那包覆在軍綠色燈心絨外套裡的身板明顯厚實了些,宮治淡淡地看著他,過了半晌指向他的身後,宮侑才注意到老闆已經將他們倆的甜甜圈裝袋完畢,於是他跟宮治給了錢,一人捧著一份甜甜圈,站到巷弄裡,繼續凝視著彼此。
「⋯⋯你是要看多久?」宮治伸手在宮侑的眼前揮了揮。
「治?」
「為什麼不撒糖粉?不撒糖粉的甜甜圈不能說是甜甜圈吧?」宮治指向宮侑手裡乾巴巴的甜甜圈。
「可是我不能吃⋯⋯」
「不能吃的明明就是整個甜甜圈,只少糖粉有什麼用。」宮治忍俊不禁,大口咬下自己手裡撒上雙倍糖粉的甜甜圈。
「可是我很想吃啊⋯⋯治你還沒回答我⋯⋯你、你怎麼會在這裡?」
「好啦,怎麼講話講到一半就哭成這樣?」宮治抬起手,抹掉他臉頰上的淚水,宮侑這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他竟毫無意識地哭了出來。
「那你等一下分我吃一口甜甜圈。」宮侑動了動嘴唇,只吐出這一句話。
「自己不會再去買一份?」宮治眉頭緊蹙,望著宮侑那一雙淚潸潸的蜜糖色雙眼,終究是將手裡的甜甜圈湊到他嘴邊,「唉,就一口。」
宮侑咧嘴笑出聲,儘管他知道自己此刻混雜著鼻涕跟淚水的顏容肯定難看到不行還是笑了,他吸了吸鼻子,隨意用手背擦掉鼻涕跟眼淚,一如既往地想要張大嘴巴一口氣吃掉一大半,末了他還是縮小了嘴型,輕輕地咬去一小塊邊角。
酥脆的外衣在嘴裡嚼得嘎茲作響,雙倍的甜膩糖粉補足了方才的苦澀與眼淚沾上嘴巴的苦鹹,宮侑想振作地說出一句「好好吃」,眼淚卻又不爭氣地撲簌簌掉了下來,沾溼了整張臉跟圍巾,縱使他馬上拉開握著甜甜圈的手,仍有幾滴淚珠落在甜甜圈上,上頭的糖霜因而結成小小的塊狀,糖塊隨著宮侑的晃動掉進他剛才咬開的洞裡,原先空心的甜甜圈一點、一點地,緩慢而微小地被糖粉填補了起來。
宮治沒有說話,他接過宮侑另一隻手上沒有裹上糖粉的甜甜圈,咬了一口,同時很輕很輕地,抹掉他的兄弟從未停下來的眼淚。
*
宮治在來以前想了很多,兩年多未見,宮侑會是什麼樣子?法文流利到能夠跟隊友吵起架來了嗎?放假的時候會在酒吧與漂亮的法國女性之間流連忘返嗎?或是都一個人窩在宿舍,想著日本好好吃的米飯邊想念邊哭?
他第一句話要跟他說什麼?是生疏到先問他這幾年過得怎麼樣,還是該表現得稀鬆平常,像是那些年他們在飯糰宮的日子,調侃他比賽怎麼發球失誤這麼多次?
最後宮治只是擦完他的眼淚之後,又用手指抹去宮侑嘴唇上的一圈糖粉,動作熟悉地如同為他拿掉掛在唇角上的飯粒。
「你欠我一個裹滿雙倍糖粉的甜甜圈,既然到了法國,布丁存摺就換成甜甜圈存摺。」
聞言,宮侑笑彎了眉眼,眉宇之間捎上一縷秋日暖陽,照耀著眼角的淚珠。
太陽自那厚重的雲靄洩了一地曙光,積雲緩緩消散,空氣中的水滴悄悄蒸乾,整座城市依然照常運作,一切卻都有了全新的模樣。
宮侑遲來的雨季終於來臨了。
by 匿名排民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