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long as the seasons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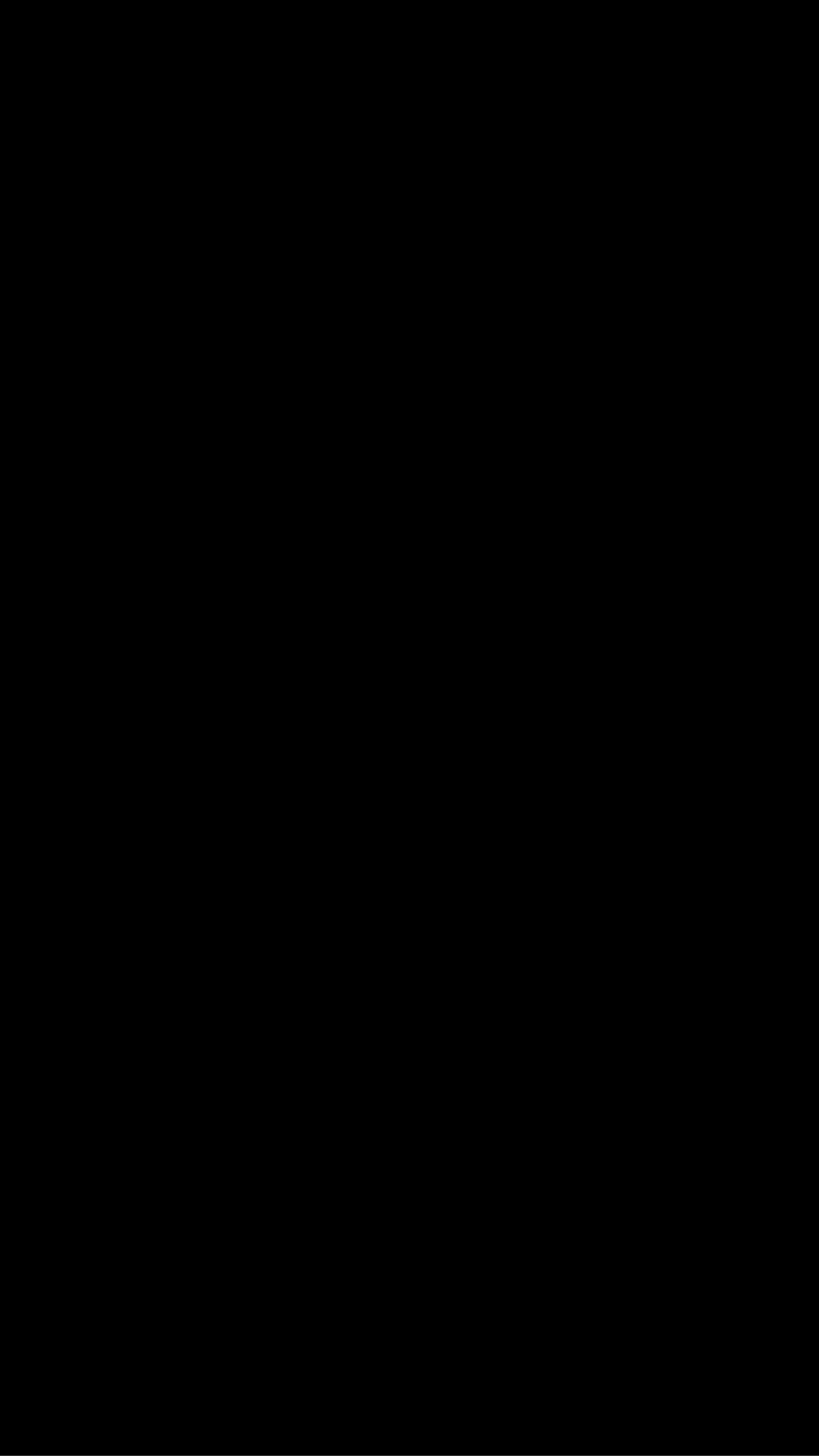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1日
- 讀畢需時 5 分鐘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 葉卡捷琳堡的四季分明,縱使來之前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親身體會到那極端的溫度後黑尾還是沒出息的蜷縮在棉被裡。 夜久走出浴室,看見床上的棉被生物後無奈地笑了笑。 「可別小看俄羅斯的冬天喔。」 「我沒有!我還有問你要不要帶暖桌!」 「白痴嗎,你要怎麼帶上飛機,房子就這麼大你打算把暖桌放在哪?」 黑尾連腦袋都縮進被子裡,反駁的話語隔著層層布料變得模糊不清。 冷是真的冷,不過可憐兮兮的模樣大概有一半是裝出來的。諳知男友的小心機,夜久還是走到床邊,隔著棉被抱住正在撒嬌的黑貓。 「所以說你為什麼偏偏要挑這個時候來啊。」 「我又不是來觀光的,想見男朋友還要挑時間嗎?」 夜久懶得和他辯,只顧著把棉被團用力往裡面推,黑尾乖乖往旁邊滾一圈讓出更多空間。 夜久才剛爬上床就被從棉被中探出的手拽進被窩,剛洗好澡的他全身都是暖的,縈繞在鼻尖的洗髮精香味和自己的一樣,黑尾忍不住多蹭幾下。 夜久被他弄得很癢,不顧黑尾的哀嚎奮力把人推開,堅持把棉被往下拉到肩膀,免得兩人窒息上隔天社會版新聞。 喬了個舒適的角度躺好後才張開手,黑尾馬上就抱了過來,夜久一手回抱住對方,另一手在床頭摸索一陣,找到檯燈開關後按下,房間頓時陷入一片黑暗。 「現在才十點欸,這時候睡覺不會太早了嗎?」 「東京現在是凌晨兩點。」 「為什麼要在俄羅斯過日本時間啊!」 「想睡就睡哪來那麼多為什麼,你是不睡午覺的幼稚園小孩嗎!」 「我是啊!」 「你只是個幼稚又煩人的大叔!」 什麼大叔他還沒三十歲呢、既然說他是大叔那就來陪大叔做點兒少不宜的事吧。 彷彿是料到黑尾想說什麼,夜久壓根不給他機會開口,丟下一句「你不睡的話我要睡了」就閉上眼睛。 黑尾不敢置信地看著他,在寒冷的國度待久了連帶著性格也會變得冷漠嗎?不是隔著螢幕或電話,許久未見的男友就躺在自己身側,夜久居然不為所動? 黑尾本來想撓他癢,但怕被壞脾氣的貓踢下床只能作罷,作為代替他默默收緊環在對方腰間的手表達抗議。 黑尾上次過來是在夏天最炎熱的時候,葉卡捷琳堡的夏季可愛太多,公共場合幾乎沒有冷氣電扇是小事,可怕的是偶發的大雨還有日落之後溫度驟降,極端的溫差令人產生彷彿身在不同國度的錯覺。 那時夜久也說過類似的話,可別小看俄羅斯的夏天。 但黑尾發誓真的沒有,他無非就是想體會一下,不是網路上部落客的推薦也不是旅遊節目的介紹,而是真實存在於夜久衛輔生活裡的日常風景。 即使清楚所見遠遠不及對方所經歷的刻骨銘心,可他喜歡的人在那裡,再平凡不過,枯燥乏味讓人懶得多看一眼的畫面,也會成為令他渴望親眼見證,然後放在心上珍藏一輩子的美好。 兩人相擁的姿勢讓黑尾看不見夜久的表情,但黑尾足夠理解他,果不其然在幾秒鐘後聽見懷裡傳來一聲嘆息。 「你都不覺得冷?」 「怎麼可能,只是稍微習慣了。」 伸手把那頭亂糟糟的黑髮揉得更亂,不同於手上的力道之重,夜久的聲音很輕。 「剛開始都是這樣,習慣就好。」 雲淡風輕的話語和背後的深意都讓黑尾感到眼角酸澀。 科學家早已證實二十一日養成習慣只是迷思,漫長而難熬的過程裡,日復一日想辦法把靈魂騰出一塊空地安放並不屬於自己的部分,成功與否折磨都不會減少,還有更多難以習慣的事,不論如何都沒辦法習慣的事。 「你記不記得那個雪球夾?」 夜久忽然提及與剛剛無關的話題,意料外的反應令黑尾愣了一下,儘管困惑他還是在思考後應道:「你在社辦找出來的,貓咪造型的那個?」 「嗯。話說回來為什麼社辦裡有那麼多奇怪的東西啊,學長畢業前都沒有整理嗎?」 「我才覺得虧你能挖出那些。」 黑尾輕聲笑了起來,他想到以前夜久認真翻找東西的模樣,幾乎上半身都要鑽進櫃子,還真的挺像一隻貪玩的小貓。 「我還記得你第一件事就是拿來夾我的臉。」 「先試看看能不能用啊,」夜久也笑出來,抬起頭迎上他的視線時眼睛是亮著的。 「你做的山本超像的。」 「除了山本外其他人根本捏不出來,最後都是用畫的。」 「我說把我弄得帥氣一點,你就把那隻雪貓的頭壓扁了。」 「我不是道過歉了嗎!要怪就怪你那顆頭有夠麻煩!」 隨著對話的進行,那些早已遠去的往昔在夜裡變得清晰,彼時距離社團活動還有一點時間,夜久興致勃勃地把他拖出門,老大不小的兩人蹲在社辦外面玩雪,一隻隻雪白的小貓乖巧躺在腳邊,可他總覺得臉頰紅通通的戀人笑起來更加可愛。 已經想不起來是誰的提議,他們開始對小雪貓伸出魔爪,想弄成自家社員的樣子,在慘叫聲中一連毀了幾隻無辜的小貓後總算放棄用雪塑型,改拿樹枝給小貓畫上表情。 一開始還吵著誰畫得醜誰畫得比較像,到後來黑尾幾乎放下樹枝,撐著臉看夜久認真的側臉,口中吐出的白霧消散在冷空氣之中。 身後的積雪襯得陽光閃閃發亮,夜久完成後偏過頭看向他,笑得很好看。 黑尾在這一瞬才真正理解炫目一詞的意思,趕在後輩們發現然後加入前,在那片雪色中吻上他。 「還冷嗎?」 黑尾這才從回憶裡抽離,緩慢眨兩下眼睛。 「冷啊,不過沒那麼難受了。」 「對吧。」 夜久的表情很得意,黑尾差點要以為躺在懷裡的仍是那個玩雪玩得不亦樂乎的少年。 「這招每次都很管用。」 看著黑尾愣怔的神情,夜久忍不住笑出聲:「就像你說的那樣,一個人要怎麼捱過這種鬼天氣。」 他才沒有說,然而黑尾知道夜久也足夠理解他,並不是很意外那些心思被揭穿,只是眨眨眼睛,很慢的應了一聲嗯。 言語太蒼白無力,有那麼多重要的事難以啟齒,有那麼多想訴說的事一旦說出口就變得多餘。就像夜久除了天氣以外的抱怨都絕口不提,因為沒有必要也因為他甘之如飴,於是那些心疼和不捨,沒能參與或陪伴的遺憾,通通被黑尾用力畫上叉叉,他沒辦法也不打算告訴夜久。 然而夜久還是知道了,然後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他,就算相隔兩地也依然是他陪著他度過長夜漫漫,東京距離葉卡捷琳堡六千多公里,誰都沒有走遠。 黑尾後知後覺感到疲倦,身體和精神都是,不只是因為長途飛行或是環境,更像是一場盛大的流浪終於落幕,他覺得自己的某部分遺失很久很久,在這個晚上通通被找到、被溫柔擁入懷。 安心感和疲憊一同湧上来,黑尾眼皮厚重卻捨不得睡,還想說些什麼,但似乎再多說一句、一百句也不夠。 曾經覺得不能訴諸於口的都聚集在胸口,捎來一陣蟬鳴似的鼓譟,想要傾訴、想要被聽見,每一句話都要用千萬句補充,一個細枝末節都捨不得漏掉。 該從哪裡開始呢? 黑尾微笑著閉上眼睛。 by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