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把你留住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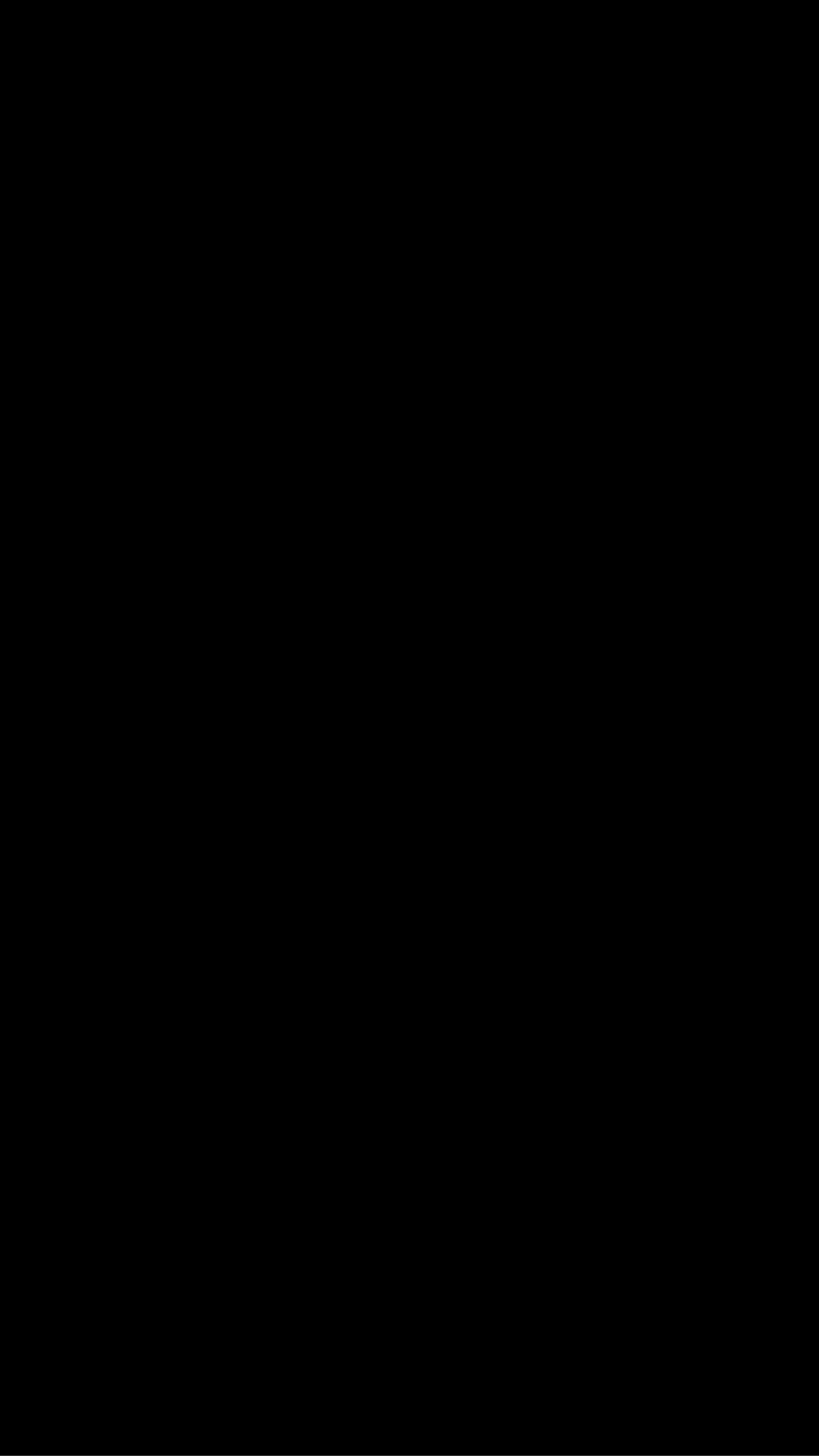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9日
- 讀畢需時 13 分鐘
Warning:
幕末,新選組背景,人物代指有
內含極微量大將組
閱讀過程中如有任何不適請迅速退出,筆者不負任何責任(?
Bgm:
Sundaland of Mind —— Tokyo Blue Weeps
慶應三年,春,西本願寺。
粉白的花朵一簇簇的團在枝枒上,風一來,花瓣就像雪一樣緩緩飄到地面,引人駐足欣賞——本該是這樣的。
初春的空氣對一個癆病患者來說實在太過寒涼,喉間漫上的癢意讓及川徹不得不停下自己的步伐,扶著盛開的櫻樹一陣猛咳。
一塊疊的方正的手帕悄悄地遞到及川面前,被他毫不客氣的接了過去。柔軟的織品不像他交往的那些祇園姑娘一樣染著各式的花香,而是帶著單純到可以說是毫無矯飾的淡淡皂香——就如其主人牛島若利一般。
自若地將不屬於自己的手帕塞回袖袋,及川舔了舔因久病而乾燥的起皮的嘴唇,開口:「你要走?」
如果說有什麼值得療養中的及川不顧病情也要起身追問的,那就只有關乎新選組發展的大事了。
「及川,你不該出來。」
牛島的語氣並不溫軟,但對於相熟的人來說,他眼中的那抹擔憂實在明顯的讓人忽視了言語上的缺陷。
不過及川並沒有為此動容,他現在只專注於得到答案。
「回答問題,小牛若。你要離隊?」
牛島定定地看著及川,給予肯定的答覆。
相識多年,雖然及川看上去總是對他挑三揀四,口中沒有一句好話,動不動就跳腳高喊自己被他氣到,但其實對方很少真正動怒,只不過現在,及川那雙溫潤的眸子裡像是蓄了層厚重的陰雲一樣,沉壓的讓牛島心裡發慌——儘管對及川的反應有所預料,他仍為此感到手足無措。
兩個同樣英俊挺拔的男人在紛飛的櫻花瓣下對立相視本該是一副好光景,但比起這樣溫柔的場景,巍峨雪山下結冰的湖面顯然更適合現在的他們。
「你要離隊。」及川確認般復述,每一個音節都咬得極為清楚。
接著他「噢」地一聲拖得老長,狀似理解,語氣平靜卻無端帶著幾分肅殺:「小牛若也覺得勤王派比較好嗎?」
牛島抿唇,想張口說些什麼時卻被從簷廊傳來的宏亮聲音打斷,「找到了!喂黑尾——及川在這裡!還有牛若!」
穿著淺蔥色山形羽織的木兔黑尾聯袂而至。
「及川你別仗著自己生病不會被岩泉醫生揍就亂跑啊。」木兔埋怨地說,完全沒察覺到及川和牛島之間湧動的暗流。
見到他們,及川很快恢復平常那嘻皮笑臉的樣子,吐槽:「你試試整個月躺在床上不能練刀的感覺就知道了。」
木兔當場蔫掉。
黑尾倒是注意到了兩人的異常,但不願去管,知道牛島要去東山護陵時他就知道及川會鬧彆扭,但看情形再不把他們分開他擔心今天要見紅。
「這可不是你逃避喝藥的理由啊及川。」他說著,一邊準備把及川拽走。
這個時候及川滿臉乖巧,毫無反抗地被黑尾拉著。只不過走了兩步後又回頭,對著牛島笑得燦爛:「貧瘠的土地是無法結出豐碩果實的……是嗎?」
及川和黑尾的身影很快消失在簷廊上,櫻樹下只餘滿臉疑惑的木兔和像是被定住的牛島。
牛島走的那天及川沒有去送。
他知道牛島在門外坐了很久,從晨光初綻到日光漸盛,映在紙糊障子門上的身影越漸清晰,直到對方不得不啟程,及川緊閉的房門都沒有露絲一絲一毫的縫隙。
脫掉新選組羽織的人不再是他的同伴,而是需要拔刀相對的敵寇。
只是那句「好好保重」卻像是被銘刻在腦海裡一樣讓及川心生鬱氣,加上日前和牛島對峙時受了風,當晚就發了高熱,鬧的屯所一陣人仰馬翻——不過這些都和牛島沒有關係了。
熬過了乍暖還寒的春三月,及川的身體也漸漸好了起來,到了七夕祭的時候甚至能和隊士們勾肩搭背地喝花酒。
不過他們尋歡作樂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
薩長同盟步步緊逼,小動作不斷,將軍上書奉還朝政後更是氣焰囂張,及川夢中盡是些刀光劍影,彷彿隨時都有人會殺進屯所來。
但又有誰膽子那麼大敢半夜擅闖新選組駐地呢?
唰——!藏在枕下的短刀出鞘,刀刃撞上來人的包袱,衣物布料散了一地,「是我,牛島。」
「嗯?藏頭藏尾的人及川先生不認識喔。」及川說著,護身刀卻是好好的收了起來。
牛島見狀,鬆了一口氣。他們要是真打起來,整個屯所的人都會被他們吵醒,這麼一來他悄悄回來的事就瞞不住了。
他看著及川,屋內黑暗也不影響他描摹眼前人的輪廓,「你瘦了。」
「護陵衛士伙食還挺好。」及川陰陽怪氣。
「能讓你摸進來,看來今晚值夜的人都該切腹謝罪。」
牛島沉默了一瞬,說:「是副長放我進來的。」
這句話資訊量不小。
他們家的魔鬼副長可不是會顧念舊情的人,雖然不明事情原委,及川還是本能的選擇了相信。
不過他還是氣急敗壞地質問牛島:「放就放,難不成你摸到我房裡也是他讓的嗎?!」
還記得要壓低聲量已經算及川很給面子了。
然後牛島異常誠懇地點頭,道:「他說你夜裡容易起燒,最好有人就近照看。」
「真聽話,你也不怕染病。」及川冷哼,也沒說一些讓牛島滾回自己房間去的話。
「不會的。」這回牛島反應很快,看出及川沒有要繼續和他對峙的意思,便俐落地從櫥櫃搬出被褥鋪床。
最後及川只這麼說:「睡離我遠點。」
頭腦昏昏沉沉,及川知道自己八成又發燒了,染上肺癆後他時不時都要病一場,不是什麼大事,熬一熬,天一亮讓人備點熱湯就好了,他想。
黏在額上的頭髮被人輕輕撥開,及川抓住對方的手。
誰?及川嘶啞的問,勉強睜開眼只看到層層疊疊的重影。
是我,牛島。
不知道過了多久,及川感覺自己被半扶半抱著褪下寢衣,擦去一身熱汗。
鼻腔傳來一陣令人安心的,像他藏而不用的那條手帕的味道,這讓及川像頭幼獸一樣,本能地朝讓自己感到安心的地方拱蹭。
這太過了——牛島艱難地想。
及川從未在他面前展現過這麼依戀的姿態,哪怕他們過去曾在酒酣耳熱之際逾越了同僚乃至於友人的界線,哪怕他曾見過他淚眼婆娑面容潮紅的無力姿態。
因為呼吸不暢而微微開闔的嘴唇、顫動的濃密睫羽和英朗眉宇間罕見流露的脆弱都讓牛島內心某處悄然塌陷。
直到胸口一陣憋悶牛島才驚覺他竟是下意識的屏息了。
極其小心的吐出濁氣,他害怕這難得一見的奇遇會因為他的魯莽消失。
而燒得糊塗的及川卻在這溫柔但深沉的目光中逐漸睡熟。
只是朦朧間感覺有什麼溫熱的東西輕輕地碰了碰他的眉心。
及川醒的時候,房內空蕩蕩的看不出有人留宿的痕跡,腕骨揉按著額角,回想起昨夜種種的他坐起身,只覺得一切都不夠真實。
紅的灼人的落日將天空染成一片火燒的霞色,放在廊上食物已經涼透,看到漆色托盤上放著紅楓葉,及川略勾了下唇角,這又是他哪個同僚彆扭的關心?
收起紅葉,及川一手端起托盤起身,另一手掖著被換下的衣物離開了房間。
填飽肚子,又把自己拾掇的乾淨清爽的及川哼著調,慢悠悠地走在廊上,甚至饒有興致地在迴廊處佇足片刻,這麼一拖再拖,回房時已經夜幕高垂。
障子門拉開一條縫,果不其然一片黑,及川眼一瞇,終於在角落抓到刀刃反的白光,再定睛一看,一身黑的牛島若利就坐在那給刀手入。
「穿這麼黑是等著人來踩?」及川沒好氣道,強迫自己壓下那股莫名的歡欣。
牛島沒什麼表情地看他,眼神是熟悉到令人血壓飆升的無辜。
燭光搖曳躍動不熄,及川和牛島各自佔據房間一角,安靜的以米紙擦拭視作第二生命的刀劍。
打粉棒輕拍刀刃反覆擦拭,及川舉刀,看著越發光亮的刃身映照著自己的面容,滿意地點了點頭,接著他轉身欲取矮桌抽屜裡的丁子油,燭台旁靜靜躺著的紅楓撞進他眼底。
這不對。
今天太靜了,不僅沒有酒鬼的鬼哭狼嚎,廊上的打鬧聲也比平時小了不少,就好像少了人似的熱鬧不起來,這讓他想到元治那年的池田屋和禁門……那時候也是這麼安靜。
及川眼神一凝,猛地轉頭逼視牛島,「他們行動了是嗎?伊東?」
在副長許可下出現在他面前的牛島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牛島輕輕地點頭。
「那你呢?是來監視我,別讓我搗亂的?」
「及川。」牛島開口,眼神沉沉地注視他,「你不能再受風了。」
所以我是又被拋下了嗎?已經沒有出劍的資格了嗎?因為他會拖累其他人?
「一柄不能出鞘的劍,和廢鐵有什麼區別?」及川的臉色白的像紙,他閉上眼睛,狠狠嚥下那股油然而生的無力和恐懼。
隔天一早,新選組內部迎來了牛島的歸隊,伊東死亡的消息也從油小路擴散到整個京都。
「副長助勤牛島氏,因公出差,本日歸隊,並回復以前職務。」
因公出差……及川垂眸,沒有從眾地歡迎牛島,而是自顧自地把玩著佩刀上的流蘇。
歡迎很快變成閒聊,往常公事公辦的副長也難得地沒有立即打斷這些和會議無關的閒話,只是靜靜地在上首抿茶——得用的隊員歸隊,還替將軍剷除了一個威脅,這大概是這陣子以來最讓人舒心的事了。
只是當木兔說起昨晚怎麼將伊東的屍首從本光寺挪到油小路,又是怎麼將他當作餌料把前來收屍的御陵衛士們像切蘿蔔一樣料理了時,越聽越覺得刺耳的及川終於站起來,在一眾幹部或疑惑或擔憂的目光下面無表情地開口:「抱歉,我不舒服,先下去休息了。」
再待下去,他就該嫉妒瘋了。
牛島第一次不顧進行中的會議追了出去。
「及川他……」木兔眨巴眼,破天荒的讀懂了黑尾的暗示,乖巧地做了一個閉口不言的姿勢。
與黑尾交換了眼神的大地輕咳了一下,將跑偏的會議拉了回來:「及川的事就交給牛島吧,他會處理好的。」
及川悶頭疾行,一點也不想理會追在身後的腳步聲。
他本來是想找個僻靜的地方自己待著生悶氣,只不過總有人看不懂臉色。
驟然停住腳步,他轉頭,咬牙切齒:「你要跟到什麼時候,及川先生現在心情很不好。」
「我知道。」
及川這一停,本來就跟的緊的牛島差點沒煞住,好在他反應快,往旁偏了一步,這才沒一頭撞上去。他略抬了抬手,把掛在臂彎的羽織亮了出來,「你忘了這個。」
見及川面色鐵青沉默不語,牛島索性直接替他把羽織穿上,「手。」
及川不理他,只是自顧自地說:「我很嫉妒你,小牛若。」
牛島沒有答腔,好像眼下只有把及川裹進羽織裡才是正事。
「還有小黑、木兔和澤村⋯⋯」及川數著人名,「我嫉妒你們可以為將軍效力、可以揮刀,現在的我一點都不像個武士。」
他厭惡那個越發乖僻的自己。
也痛恨那個會嫉妒同伴的自己。
「你也是武士。」牛島說。他把及川的手塞進大袖中,又低頭撫平布料上的皺褶。
「現在也還是?我已經忘了自己多久沒砍人了。」
像是沒聽懂及川語氣中的介懷一樣,牛島瞥了眼及川繫在腰上的兩把刀,說:「只要你還能揮刀就是。」
牛島過於理所當然的樣子讓及川心裡的那些煩躁和鬱氣都顯得無理取鬧起來,抿了抿嘴,他想道謝又有些難為情,最後顧左右而言他了起來:
「我今年沒有吃到七辻家的櫻餅。」
似嗔怪又似撒嬌,這就算及川拐彎抹角的示好了,每年春天他們都吃的,今年牛島缺席,他也沒想過單獨去吃。
「明年我們一起,還有三色糰子。」牛島認真應下,他也很懷念巡邏完和及川一起飲茶休息的時光。
順坡下了台階,及川自在多了,他把剛剛席間未出口的疑問托出:
「我搞不懂,怎麼會是你去?」他還以為牛島真的另謀出路。
「因為我不是試衛館出身。」牛島回答。
因為不是近藤門下,又是左手刀,轉投伊東時理所當然地被當作是因為在新選組不被重用而心生怨懟……說起來,時常挖苦他的及川可是居功甚偉。
「會叫的狗不咬人⋯⋯」及川喃喃,嗤笑:「你這隻啞巴狼倒是一口就把伊東搞掉了。」
牛島眉梢輕輕揚起,只否認了前半句:「我不啞。」
「吶小牛若,難得天氣好,練一場?」
一走走了大半年,牛島甚想念及川和他的劍術不假,但又實在顧惜他的身體,內心拉扯,一時間難以斷決。
及川剛經勸慰,又因為身體的原因,平常被同伴們拘著靜養,早等不及拿剛回來還沒被醫生耳提面命的牛島試刀了,「怕什麼,我還不至於手合一場就死掉。」
他總是有把人牽著鼻子走的能耐。
對著牛島尤甚。
高手過招,往往幾回合就見分曉,不過這對牛島和及川則不然,他們相識太久,對彼此的一招一式都太過熟悉,練起手來總要打到其中一方武器脫手才罷休。
以刀隔住及川的三段突刺,牛島還未反擊,就見及川身形一晃,幸好及時用刀撐住才沒直接摔倒。
「及川!」牛島焦急喊著,上前撐住及川。
「那麼大聲幹嘛?我還沒死⋯⋯」及川扯了扯嘴角,臉上是牛島孰悉的倔,接著他面色一變,低頭摀嘴,蓄謀已久的不適強行掙脫了身的囚籠,帶著血氣一鼓作氣地宣洩出來,「咳咳咳咳⋯⋯」
點點腥紅落在地上,把牛島的眼睛灼的發紅,他想碰他,又怕自己不知輕重,手足無措的樣子根本看不出平時的沉穩。
「我去找醫者!」
「不許去……」沾滿血沫的手抓住牛島衣襟,又無力的滑落,留下一道蜿蜒的痕跡。醫囑上的靜養從來不是說笑,及川清楚得很,這副病體早就撐不住任何劇烈運動,一場期盼已久的手合也不行。
但他勇於承擔自己招致的苦果,並欣然接受。
「你表情好醜……」
及川的呼吸粗重又破敗,牛島在那瞬間想起了被他們割破喉管的浪人,他們倒在地上痛苦的樣子和現在的及川隱隱重合,這讓他抑不住心慌,又不得不強壓下那份不安,儘量地平穩開口:「這樣不行,讓我去找岩泉,好嗎?」
牛島很少用這種語氣和人商量,如果不是及川,他大概這輩子都不會用這麼輕柔小心的語氣說話——但現在沒人在意這個。
及川像是被他打動,輕聲妥協:「晚一點。」
這難得的妥協反而讓牛島眼底的擔憂更濃,而及川接下來的話則讓牛島心下一沉,他問:「小牛若現在還覺得我是武士嗎?連刀都握不穩了喔?」
「武士之魂不在其形。你是,一直都是。」
及川沒有接話,只是笑了一下,然後頭抵在牛島肩上,把全身的重量都交托出去,「再待一會就回去。」
「……好。」
慶應四年,春,淺草。
拔起木栓,岩泉一手按在刀上,小心翼翼地拉開門,在確認來人後呼出一口氣,讓出過道。
「他還好嗎?」牛島摘下斗笠問道。
「就那樣吧。今天精神不太好,還在睡。」見他皺眉,岩泉苦笑,「你知道我只能盡力調養。」
只是再怎麼用藥也只是延命罷了,醫者心想。
及川在去年和牛島切磋之後就一病不起,直到十二月的雪夜,近藤局長於伏見街道遭到御陵衛士殘黨槍擊負傷,他們一起被轉移到大阪城休養。
至元月,新政府與幕府的衝突終於爆發,四日後以幕府軍的戰敗告終,新選組屢戰屢敗,至甲州勝沼之戰後全原返回江戶。
而及川,正是被藏在岩泉位於淺草的宅邸裡。
泡了壺茶,岩泉看向難掩疲憊仍端正跪坐的牛島,「戰況不容樂觀,江戶人心惶惶。」
看著茶湯裡自己的倒影,牛島覺得自己的聲音平穩的像是個置身事外的人:「近藤局長在流山被捕,皇軍⋯⋯拒絕赦免。」
岩泉心一顫,下意識往及川房間瞧——毫無聲響。眉心擰出一道深痕,他壓低聲卻難掩氣急:「怎麼回事?土方先生呢?」
牛島未語,他捧著茶盞望向廊外,被煙硝塗抹過的天空下粉白的櫻花已經敗得所剩無幾,枝梢伶仃幾朵更顯落魄——他這才發現京都的櫻和江戶如此不同。
不過一年的時間,他們就從幕臣變成朝賊。
靜坐許久,牛島終於開口:「近藤局長的事,別告訴他。」
那個他是誰昭然若揭。
岩泉嘆氣,一臉「你可真會為難我」的無奈,「我不說,及川有可能不問嗎?」
忽然,牛島偏頭,低啞又綿長的聲音傳進他們耳中,「小岩——誰來了?有近藤先生的消息嗎?」
「我去吧。」牛島按了按岩泉肩膀。
真是怕什麼來什麼,岩泉腹誹,也跟著起身,「我去熬藥。」
房門被拉開,剛醒沒多久的及川抬眸,在看到來人時不自覺帶出笑意——但語中還是帶著刻意的嫌棄:「原來是小牛若啊。」
然而開口時涼風入喉,咳得撕心裂肺,那股佯裝的嫌棄全化成了自己的難堪狼狽。
儘管對及川的病容有所推測,但當真的觸碰到那對嶙峋的肩胛時,牛島還是被磕的心裡發疼。他伸手碰了碰案上水壺,在確認溫熱後倒了杯水要喂及川。
就著牛島的手抿了兩口水潤喉,及川緩過來後抓著他問:「什麼時候到江戶的?其他人呢?近藤先生?」
牛島搖頭,撿著及川最在意的問題回,端肅道:「我們和近藤局長在流山分開了。前天到的,整備完就過來了。」
只有他知道自己說這些話時內心有多忐忑,在應對及川這件事上他從來都信心不足,尤其這次還是朝他隱瞞。
及川凝視牛島,像是在思索他話語的信度般沉默了一會,然後啟唇自嘲:「是嗎,真可惜,現在的我可是看一次賺一次喔。」
牛島鬆了口氣的同時又不贊同地看他,「別說這種話。」
「我也沒說錯不是嗎?」及川笑著,眼裡有長期臥床的疲倦和落寞。
逼著自己不去想及川的病,牛島拿出來前在街上買的點心,攤開油紙,裡面放著的是及川心心念念的櫻餅和三色糰子。
「臨時在街上買的,明年春天再回京都吃吧。」
沒和牛島辯駁他有沒有明年這件事,及川咬了口櫻餅,又把糰子懟近牛島嘴裡,半是轉移話題半是控訴地說:「有得吃就不錯了⋯⋯小岩看到會被沒收的。」
就著窗外的殘櫻,他們慢慢分掉了這些點心。
對折再對折,及川一眼不落地看著牛島耐心地收拾掉油紙,忽然開口:「要走了?」
說完,兩個人都是一愣。
一年前的及川也是用類似的語句發問,只不過其中包含的情緒截然不同。
「嗯,等我回來。」
及川發現牛島的話語總是在誘導他做出承諾,而本人似乎毫無自覺。一股複雜的情緒忽然湧上,半酸半苦的讓他喉頭發澀。
「及川先生才不等你,等好一點了絕對追上你們。」
牛島走後,及川病情惡化,不是發燒就是嘔血,岩泉也變得草木皆兵。
具體顯現在對及川的嚴加看護上——一天三趟確認及川狀況,限制他開窗吹風的時間,以及爐上從不間斷燒著的熱水和烘暖的羽織。
然而,就算病的難以下榻,及川仍會追問岩泉戰況,這讓曾經的幕府侍醫難以應對——尤其在合夥牛島瞞著近藤先生近況這點上,他既惴惴不安又慶幸及川現今不良於行。
讓他平靜的過完最後的日子吧,別去送死,岩泉想。
近藤勇被斬首那天,及川幾乎整日都在昏睡,岩泉鬆了口氣的同時又感到幾分悲憫,之後他仍舊撿著些瑣碎的戰情唸給及川聽,比如江戶無血開城、彰義隊解散,比如新選組殘餘隊士轉往會津。
及川靜靜聽著,清醒的時間越來越短。
當櫻枝蔓出嫩綠新芽的時候,及川消失了。
藥盞匡噹落在地上,碎了一地,濺出的藥汁將榻榻米浸成深褐色,滿室澀意。岩泉看著空蕩蕩刀架,往日及川的話語不斷迴響——
「死在病榻上可不是武士所為啊。」及川笑著說,眼中有散不去的陰翳。
他駁斥:「哪怕你摸到了戰場的土,也拿不起昔日的刀,平白送死很有意思嗎?」
而及川絲毫不讓地反問:「和他們在同片天空下,卻沒碰過一捧戰場的土,小岩不覺得窩囊嗎?」
今時不同往日⋯⋯那時的岩泉這麼想,卻怎麼也說不出口——昔日新選組隊長的風采又在及川身上出現。
不過,轉眼的功夫,及川就收起了展現出的光華銳意,彷彿那全是假象。
看著架上的刀,及川笑中帶有幾分落寞:「嘛⋯⋯也要能握得住刀才行,我現在連後院的黑貓都斬不動了呢。」
撒謊,這不是還能偷溜嗎。面對掀起卻不見人影的被褥,岩泉想。
但意外的是,此時此刻他無比平靜,或許他潛意識中也認為及川徹不該囿於床榻,死於病痛。
新選組的刀,哪怕鏽了蝕了,也該折在戰場上。
將自己弄翻的藥渣清理乾淨,岩泉靜坐案前,揮筆去信牛島。
他的話像平靜又決絕的告解。
「及川走了。」
他帶著春天走了。
—完—
by 竹兮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