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貓妖比賽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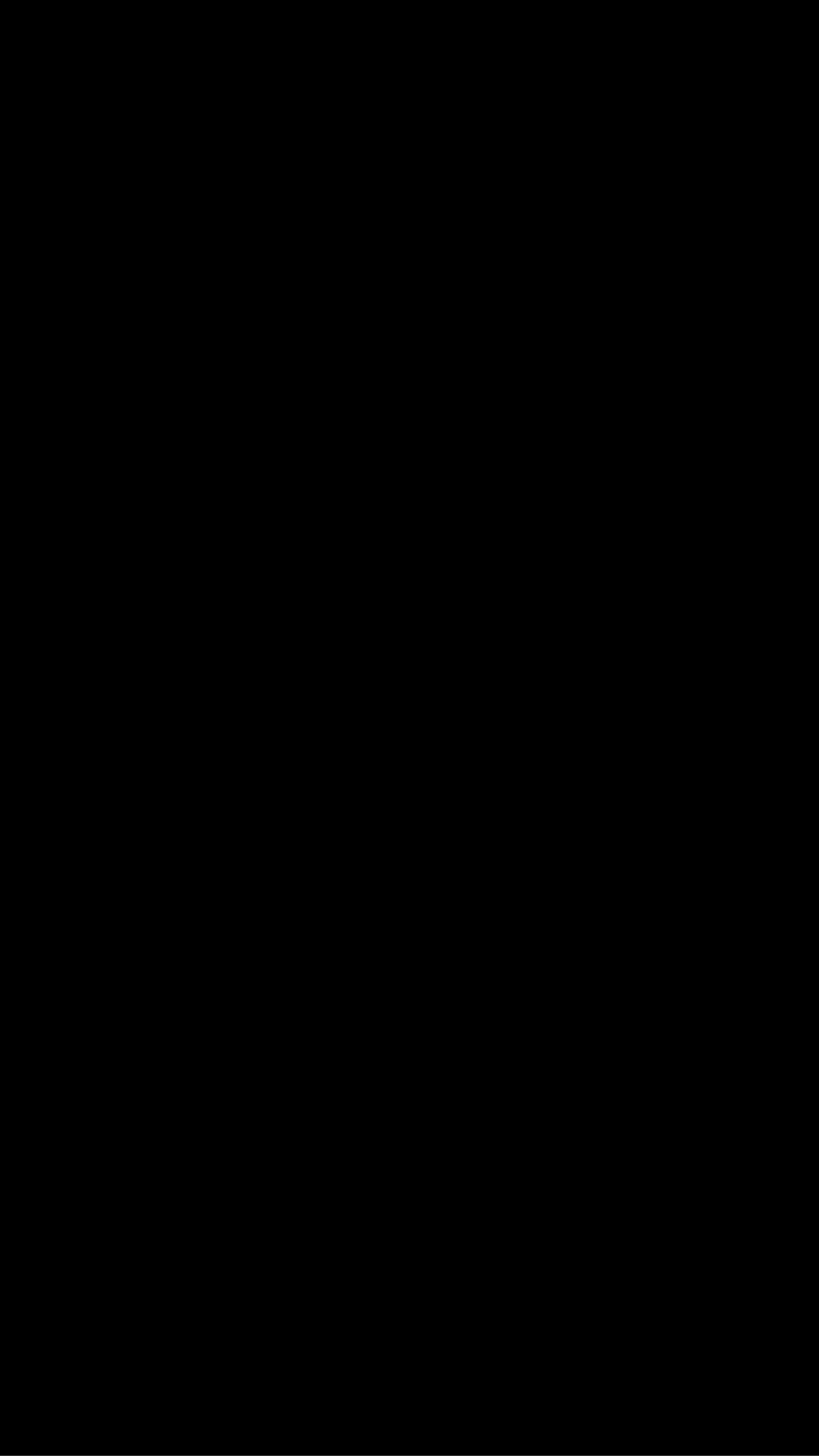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3日
- 讀畢需時 9 分鐘
烏養一繫從六十四歲那年開始,不再參與秋收。
事實上,早在他結縭數十載的妻子過世時,家裡一干小輩就已經開始不斷轟炸、要他把園子裡的事交給身輕體壯的年輕人們折騰就好,就連幾個同期都勸他在家裡含飴弄孫頤養天年,免得傷筋動骨、釀成大禍。
他只是開始有點變老、也不是老到不能動了,頤養天年什麼的自然做不到,打娘胎出生就在田裡爬滾的人忽然叫他窩在屋子裡,才會悶出病來吧!弄孫之類的勉強倒是做到了,除了早年就開始在母校帶出來的學生們都已經站穩腳跟開枝散葉之外,最大的孫子繫心後來也加入過他帶的高中校隊。可惜打得實在不怎樣,頂多強身健體。
六十四歲這一年,因為某些意料之外的病痛,他動了個小手術,住幾天醫院、和三個兒子僵持幾天、然後在他打死不願意離開老家搬去和兒女同住的堅持下,暫時住進町內的照護中心。
幾個農友都住在那,常來探望的小鬼頭們都是他這幾年教出來的小小排球手,熟人與醫護齊全,兒子女兒和孫子們又三不五時就要來路過一下,他天天都過得很熱鬧。
烏養一繫的身邊總是充滿人群,而他也習於人群,樂於人群。
回顧他短暫的六十載人生,大抵就像他打了大半輩子的排球,總是存在著最堅實的隊友、與互相扶持的夥伴。
而這之中,有個人他往往只在秋收之際想起,貓又育史,一位遠在他鄉的老友。
第一次見面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往事歷歷在目,宛若昨天。
那天很熱,他們在室外打球,記得是長虫南和白水館的其中一次練習賽。
烏養作為高大的主攻手,從一年級開始就是正選。他和白水館並非第一次打練習賽,何況兩校的學區很接近,球網兩邊都是熟面孔,只有貓又站在場邊的替補席。
他很面生,瞇著眼,貓著背,頭髮短得奇怪,雖然和他們大部分的人一樣是個寸頭,看起來卻更加毛茸茸,像坨長滿冬毛的貓屁股,讓人想上手摸幾把。
白水館的熟人曾告訴他隊上來了個轉學生,安靜又奇怪。監督說他不錯,就是身形太嬌小,隊內練習是都還跟得上,但比賽沒上過幾次場。
打得還行嗎?那要打過才知道,烏養沒有多想,他對沒交過手的球手一向不多想,反正場上見真章,真厲害的總是會碰頭。
那天兩校約好模擬決勝賽,上場的全是正選,打三局,開賽後兩邊平分秋色,但烏養那天手感很順,他覺得第三局應該可以贏。
直到第三局貓又育史上場。
不管怎麼打,這傢伙都會再把球接起來。明明有幾次烏養覺得自己已經突破防線了,但球就是又彈回來。
太沒勁了!這傢伙,到底打不打?
烏養一面火冒三丈地扣球,一面在心裡罵自己,是啊,排球就是比誰能讓球落在別家場子上的運動,你管人家怎麼打。
最後輸了,一敗塗地。
烏養不是滋味地洗著手,心裡想著,勁敵。
是不是該說說話認識一下?畢竟都是二年級,以後應該會再對打。
沒想到卻是轉學生帶著高深莫測的淺笑先開口,「很好接喔。」
啊?烏養的腦迴路還有點轉不過來。
「多謝你,讓我的評價也跟著升高了呢。」
看我下次還不打爆你!
第一次交談,烏養根本沒有講到哪怕一句話,但貓又卻笑得開懷,彷彿他有什麼超能力,能透過那張氣到嘴角眼角扭曲的臉,聽見烏養心裡放的話,並且為此哈哈大笑。
那年他們十四歲,這就是結下孽緣的開端。
俗話說,冤家路窄,但其實只是因為他們教練和白水館的教練是同期隊友,兩校實力相當,剛好校區也近,所以除了地區預賽,他們更常打練習賽。
貓又是個擅長耍小聰明的傢伙,但是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反正只要不犯規,排球場上始終是自由的。擁有勢均力敵的對手,連體能基礎訓練都會變成一段樂此不疲的時光。
升上三年級後烏養成為隊長,縣預賽前他們又和白水館打兩次練習賽,一勝一負,他總算把內角小斜線練熟,但是貓又防守的精確度也更加提高。
那天實在很熱,是宮城難得一見的高溫,他們兩群人在戶外打到汗流浹背,拉鋸到比賽結束就被教練們忙不迭趕到水龍頭下沖洗擦汗,免得中暑。
大賽將至,身體管理容不得馬虎,連平常只洗手臉的貓又都忍不住接過肥皂,就著水龍頭像大家一樣胡亂把頭給沖一沖。烏養眼角瞄過那顆比其他人都毛茸茸了點的腦袋,最後還是忍不住在貓又拿毛巾擦乾頭髮後伸手撸過去。
瞬間,他好像看見貓又那雙總是細細瞇著的眼睛張大一點。
「幹嘛?」他轉過頭來看他。
「就…跟大花的屁股一樣,想說摸一把。」
「大花是?」
「校貓。」就是在校園附近流浪、任由學生們隨便餵一點的貓。
「喔、那摸了我的屁股是不是該負責?」貓又再度不懷好意地瞇起眼睛。
「喂!我摸的明明是你的頭,鬼要摸你屁股!」烏養大驚,連忙彈開手。
他身後的同伴們見他又被耍著玩,紛紛笑著阻止他再自取其辱。
「你明明是說屁股!」白水館的隊長是烏養小學就開始一起打球的同伴,湊過來一把勾住他肩膀,「摸屁股這個真的沒話說,負起責任啊一繫。」
貓又也就算了,童年玩伴他可沒顧忌,伸腳就去踢對方膝窩,「就說那是大花的屁股!再說摸大花屁股也不用負責。」
「哇!始亂終棄耶!」洗手台前一陣鼓譟。
「少囉嗦!喂,貓妖,別以為你老是能接起我扣的球!」烏養憤下戰帖,「下次一定會贏你!」
「我接受挑戰。」貓又老神在在地回話,再度引起隊友們一陣鼓譟,「育史說得好!讚喔!」
下一次還能更強,每次賽後檢討時烏養都會這麼想。畢竟這一顆球也被接起來了,那就是它還有不足的地方。還要更強,因為貓又也會變得更強。
烏養卯足幹勁期待預賽到來,沒想到貓又卻沒來。
穿上白水館八號制服的是原本作為替補的二年級學弟,他在第一天比賽結束後繞路去了一趟白水館,貓又的同學說他又轉學了,轉往東京的學校。
初中最後的大賽,接球的人消失在球網另一邊。那一年他們贏了白水館,輸給白鳥澤。白水館的隊長似乎還很驚訝烏養竟然不知道。
「我以為育史會告訴你。」
「啊?會什麼這樣以為啊?」
「畢竟你們感情很好啊。」
「誰跟他感情好,那可是宿敵啊!宿敵!」
玩伴沒能理解他拗執的情緒,哈哈大笑著與他揮別,烏養一個人站在田埂路中央慌亂地想。東京在宮城的西邊,夕陽也在西邊,但東京那麼遠,比夕陽更遠。如果告訴老爸他想去東京找一個人打排球,他鐵定會先被老爸打死。
但是都說過接受挑戰了,贏了就跑算什麼好漢!
「別以為你跑得掉!」烏養對此憤憤不平,只要打贏白鳥澤,高中的全國大賽也會在東京舉辦,到時候他就可以坐著校車追上夕陽。
為此得要變得更強,原本不打算念高中的他為了考上烏野拼命念書,考上後又拼命練球。書很難念,球也很難打,但他只想到未能再打一場的不甘,就願意耐著性子化解那些困難。
高一那年烏野輸給青葉城西,第二年總算如願打敗白鳥澤,前往東京的路上他志得意滿,卻是再踏入場館後才想起自己從來沒想過貓又在哪裡。
他一定會繼續打球的吧,但是待的學校又如何呢?有沒有打進全國?
開幕式時烏養拼命觀望舉著東京立牌的學校,還被主將用嚴厲眼神警告,總算在賽前找到那頭毛茸茸的捲髮。
如果大花是長毛貓,鐵定就是像頭髮留長的貓又育史那頭亂毛那樣。
「找到了!」烏養憤憤地用手指著兩年不見的老對手,這傢伙竟然還有點長高了,「貓妖給我做好準備吧!」
看著貓又驚訝又不驚訝的表情,烏養覺得自己真是幹得好,這次如果能雪恥打敗音駒就更好。
找到了貓又,烏養才終於有站上全國的感覺。全國大賽不愧是全國大賽,他們打得吃力,但也不算太糟。在東京,在同一座場上,烏野贏下第一戰,贏下第二戰,但沒有贏過三回戰,比賽一眨眼就結束,二比零。
烏野不是打得不好,相反地,他們打得比平常更好。只是能進全國的自然都是好手、好隊伍。音駒上午拿下三回戰,下午的比賽烏養也在場邊看完,音駒輸的時候他也在觀眾席上拍手。此行他收穫不少,當然也想變得更強,回去後會有很多訓練需要開始進行,但是整隊離開前,他還有事要做,於是偷著空跑去找失而復得的對手。
音駒的隊員說貓又去洗手間,但烏養卻老遠就看見那顆毛茸茸的腦袋往看台後面的階梯跑。奇怪了,貓又明明不是路癡吧。
烏養三步併作兩步朝那方向追過去,沒想到卻在全無人跡的樓梯間看見意料之外的畫面。
「育史!」他忍不住大喊。
扣著貓又手臂的男人彷彿被他的大嗓門擊中手腕似地放開了貓又,直接走掉。剩下那雙細細的貓眼靜靜盯著他,兩人面面相覷,一陣尷尬。
貓又像隻貓似地觀察著烏養,又是那副高深莫測的表情,「你錯過大喊著噁心逃走的機會了。」
「我本來以為他要揍你。」烏養下意識回答。
「揍我?你大喊是為了要救我嗎?」
「不是。」
「那不然?」
「我看你好像也快要揍他了。」
這種情況下打教練是被允許的嗎?兩人再度面面相覷,又是一陣尷尬。
「我是想。」貓又淡淡說出想法,不知為何還帶有埋怨的意思,「反正揍他也不會怎樣。」
這次輪到烏養打量著他,像在確認什麼似地。
「他也不敢怎樣。」貓又的表情看來有點倔強。
烏養長長嘆了一口氣,背靠著牆蹲下來,把頭埋在雙臂之間,貓又就蹲到他身邊。這趟來東京真是大開眼界了,他不懂的事多著,別說是貓又了,就連排球也是。
「下次絕對要打爆你。」烏養前言不對後語地宣告。
「明明輸了還真敢說啊。」貓又苦笑,「你到底來幹嘛?」
「這給你,把電話號碼交出來。」烏養遞出方才匆匆寫下的紙片。
「你竟然有這個。」
「我們町內接電話線了,我家有座機。」
「那就好,我可不想被町內廣播。」
「少囉嗦!明年你還會繼續打吧?」說好了再打一場,別想逃!
貓又凝視著烏養老半天,最後仍是一抹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淺笑,「全國見。」
這樣就可以了,男子漢之間不用計較那些枝微末節,他們說再見,烏養上校車,朝著夕陽的背面與東京揮別。這次沒有對上,但是下次一定要打爆你。
隔年,他們都沒有打進全國。球落地時,屬於他們的青春就結束了。
所幸他和貓又都開始執起教鞭。
烏養自認為沒有什麼教人的天賦,只能依樣畫葫蘆。自己做什麼有效,就讓球員們也跟著這麼做;看見別人做什麼可行,他就也讓球員們上場琢磨。
每年入夏,一群身段柔軟的小貓妖們就會來宮城踢館,貓鴉大戰的畫面樂此不疲地在町內體育館重現。
歲月奔馳的時候,他們都不知不覺地被歲月帶著跑。烏養一年到頭都忙,只有秋收過後,能得點空,在真正入冬前回味這一年經過的大小時光。
妻子的聲音變小了,他的頭髮變少了,貓又胖了,回來探望的學生漸漸從人夫變成人父,孫子突然就長過了腰。
某個秋末回過神來,二十幾年都過去了。
六十四歲這一年,他動了第一個手術,打了個電話給貓又。貓又說,剛好他明年也想退休,於是六十五歲那一年,宮城再不見貓的足跡。
但醫院住沒多久,烏養覺得自己全都好了,他又給貓又打了個電話。貓又說,待在家裡閒得發慌,於是約好全國再見,他們又回到老岡位上操兵練將。
直到去年烏養再度被送進醫院。他坐在病床上,和兒子們一塊兒聽著醫生叮囑,無奈想著他們的比賽就要結束了嗎?可是他還沒有累呢,他的勁敵也還在場上,IH打完還有春高,秋收後就要比賽。
「所以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烏養問,小兒子回過頭來責怪他,「當然是醫生說全都好了之後才能回家!」
這次連大兒子都勸他,烏養只得無奈嘆氣,讓兒子給他們的貓又叔叔打電話。
隔壁床的老頭告訴烏養,人要服老。但他不同意,貓又大概也不會同意。
東京的小小貓妖們兩年後長成大貓,如今再次撲襲而至,沒想到他那才剛長過腰的孫子,竟也帶起自己的高校隊伍。
因緣際會,垃圾場的貓鴉對決,今年如約在東京舉行。
在醫院裡,他架起觀看春高賽直播的螢幕,回憶中的第三回戰,螢幕裡,播報員一一介紹兩隊人馬,烏養看見貓又臉上那抹看似別有深意的笑。
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座體育館了,上場扣球和接發的也不會是他和他的勁敵了,原來透過螢幕看的貓又育史,是長得這副模樣。從十四歲到六十九歲,這些年來他們只顧著墊球、托球、扣球,朝著球飛的方向看,竟沒發現球也會變老。
比賽過後,貓又第一次給他打視訊電話,在鏡頭背後嚷嚷著帶隊實在太累啦,早上要練傍晚也要練,為了得到家長會贊助還得額外應酬吃飯。打完這場春高他都七十歲啦他也要退休!
烏養連忙回絕他,等你帶著那幾隻小貓打完夏天的IH後再說吧。IH之後還有集訓,集訓之後還有春高,球還在飛呢,球還會一直來。
烏養半是羨慕、半是欣慰地對著螢幕另外一頭說,貓妖,待秋收之後,大寒之前,到宮城來找我喝酒啊。
【完】
by Plurk@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