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夏(R18)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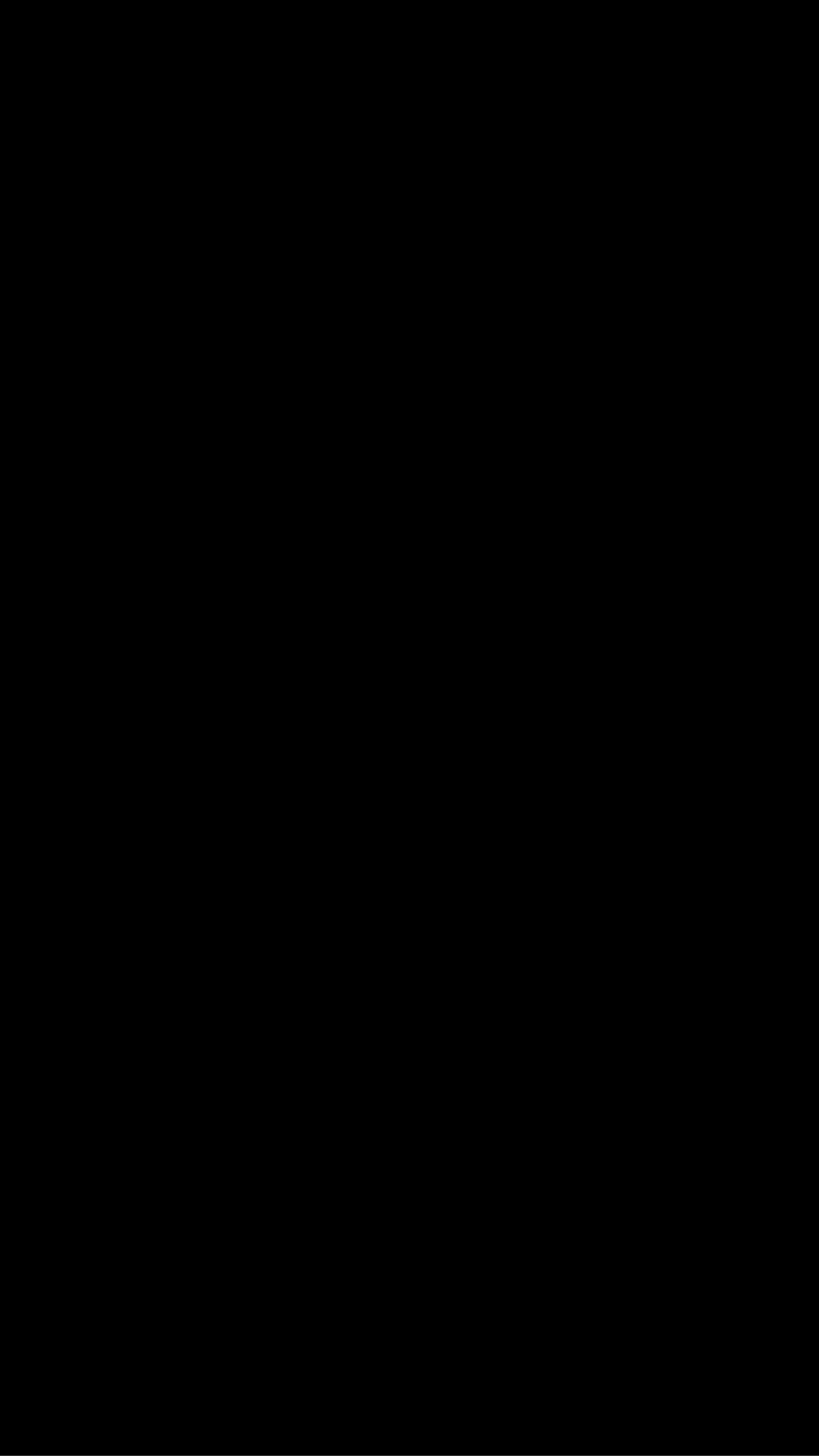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11日
- 讀畢需時 15 分鐘
※有剃毛情節,請注意 兵庫的夏天熱得讓人腦子發暈。 時近夏末,氣溫還是高得讓人一踏出門口就想縮回室內,躲在閉緊門窗開著空調的涼爽室內最好一輩子都別想出來。宮侑和宮治也想這麼做,但是他們就連假日也還是得出門自主訓練,特別是暑假──打開家門時迎面撲來的熱浪搞得宮侑也受不了,一扭頭下意識就想逃回屋內,宮治及時在他身後推了一把他的腰。 「剛才嚷著要先順路去慢跑的人不是你?要是晚到,又要挨北前輩的念了。」 「唔⋯⋯」宮侑的一條腿伸在半空中,他和宮治一樣穿著短袖短褲,但是愛美的宮侑已經在出門前就早一步在大腿及手臂抹上了防曬乳,還自作多情地追著逃跑的宮治硬是給他也抹了幾下。他的皮膚本來就白,現在抹了一層防曬乳看起來更是白得發光,滑溜溜的,有種牛奶布丁般的質感。 宮治不著痕跡地咽了口口水。早知道他就應該多吃一個飯糰再出門,都怪宮侑之前心急火燎地要拉他出門去跑步,現在卻又在家門口就臨時打了退堂鼓,一條小腿舉在半空中要伸不伸地,像隻躲在洞口探頭的土撥鼠,或者沒收好進洞穴裡的狐狸尾巴。 他又戳了宮侑的腰側一下。宮侑敏感地倒縮,扭過頭來瞪他。 「治你幹嘛?」 「沒有要提早出門的話我先進去了,我想再多吃一個飯糰。」 「不准吃!」宮侑伸手去硬扯住他的領子。宮治已經彎腰準備好要脫鞋,被扯得上半身被迫抬起,一雙鉛灰色的眼睛對上了宮侑淺棕色的眸子。 他們倆之間的差別就只有在眼珠顏色和沒染色的髮鬢毛色稍有不同,但都不是初次見面的人輕易能從外表辨認出來的。在宮治和宮侑自己本人看來,對方的臉也和自己長得完全不一樣──只有面對鏡子時他們才會恍惚發現到自己和對方長得有多像。他們花了小半會的時間、金錢和廉價染劑來和彼此以及眾人證明他們之間的差異性,但他們還是長著一張一樣的臉。 宮侑抿著嘴唇瞪著宮治的眼睛不講話。他不講話宮治也知道他的意思,他反手抓住宮侑來扯自己領子的手腕。 「那,要順路去買冰吃嗎?」他說。 從家裡到稻荷崎一段不長不短的慢跑距離讓雙胞胎都密密出了一身大汗。髮鬢全被汗水浸溼,就連髮尾也濕漉漉地滴著水。 宮侑兩三口啃完那根芒果味的冰棒,一到體育館外面就把腦袋紮到水龍頭下開始沖頭,一邊大喊好熱好熱。宮治雖然也覺得很熱但是他慢條斯理地啃完了自己的薄荷口味冰棒,舌根上一片涼絲絲的,他用舌頭緩慢地舔過口腔內側。 他們來的時間不早不晚,不出意外地在他們進更衣室準備換衣服時北信介已經到了。侑和治齊聲說了句北前輩早,北應了一聲,平淡的目光掃過宮侑在冷水下被沖得溼答答的腦袋。 「去弄乾頭髮,阿侑,不然要感冒了。」 「呃⋯⋯是!」 侑蔫答答地去找出毛巾和吹風機來弄乾頭髮。宮治站在櫃子前面換衣服,他脫掉被汗水浸透的上衣和運動褲,抖開放在一旁板凳上,然後才去穿上學校統一發放的運動T恤和棗紅色短褲。在他穿衣服時頭上頂著一條毛巾的宮侑慢吞吞地蹭過來,張口就說。 「阿治,我今天能不穿內褲打球嗎?」 「⋯⋯」宮治停下動作,斜眼瞥了他一眼。 此時北早已提前一步離開,去檢視體育館狀況及整理設備。更衣室裡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宮治想問他為什麼但他很快就想起來了為什麼,他微微挑起一邊眉毛。 「那裡還癢?」 「癢死了。」宮侑噘著嘴巴說,他噘著嘴巴時的表情總是讓宮治很想再做點別的事情。 於是他想起來自己昨天對宮侑在自己房間裡做出來的事情。 昨天的天氣照樣很熱。事實上這樣連續不斷的高溫已經持續了有整整兩個禮拜之久。宮侑每天都癱在地板上不動,跟一條忍受不了高溫的狗一樣吐出來舌頭大口喘氣,嘴裡不斷地喊著好熱。他們的母親對每天能吹冷氣的時間和條件有著嚴格的規定:只有溫度達到29度以上時才能吹,而且一次只能吹一個小時。這珍貴的一個小時雙胞胎拿來用在睡覺前讓房間裡稍微涼快一點,不然肯定熱到睡不著。 侑跟一條死狗一樣躺在地上喊熱時宮治剛好從浴室裡洗澡出來,視而不見地大步跨過宮侑平躺在地上的四肢,還順腳踢了他的大腿一下。 「你知不知道你在那裡吐舌頭的樣子真的很像一條狗。」 「因為我很熱啊!」 宮侑理所當然、彷彿完全不認為自己被這樣形容有哪裡不對地張嘴對他吐出紅紅的舌尖。宮治能看見他口腔的內側,雪白、尖利的牙齒和柔軟的深紅色的牙床。那條朝他吐出來的舌頭又厚又軟,讓宮治想到放在盤子上新鮮切好的鮪魚肚。 他頓了一秒便挪開視線,「儲藏室不是有電扇?你怎麼不去搬來。」 「我沒手。」 「⋯⋯」 正準備當他說出不管哪一句話就直接以「你自己是沒手嗎」嗆回去的宮治一時不知道該做何回答。宮侑歪過了腦袋朝他迷迷糊糊地笑,眼角和嘴角一同彎起來的樣子就像是一隻狡猾的狐狸。 「阿──治,」然後他又故意拖長了尾音喊他。原本就黏連在一起的關西腔被他黏糊糊地咬在唇齒間,拉成了一種只有在對宮治有所求時才會吐露出來的古怪音調。宮治聽不得他用這種語氣喊他,兩條粗黑色的眉毛都糾結地擰成了一團。 「你就去幫我拿嘛。」 「⋯⋯我不要。」 「難道你就不會熱?」 「誰喊熱就自己去拿。」 宮治把毛巾掛在椅背上,坐下來準備複習明天小考的內容。宮侑見不得他這麼努力假裝要認真(或者單純只是注意力不在他的身上),伸長了一條腿用小腿去勾他的腳踝。 宮治把腳抽起來,輕輕踩住了他的脛骨,宮侑發出誇張的一聲抽氣。 「蠢治你踩到我了!好痛,我覺得我腳要斷了!」 「還不是因為某人一直試圖打擾我念書。」宮治坐在椅子上斜眼瞥他,「再說,你們明天不是也有小考?」 「明天考數學,我覺得我數學挺好。」 「上次考不及格被留下來補考的人是誰?」 「誰啊?我可不知道。」 宮侑那雙糖球似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轉來轉去。宮治覺得好笑,又瞟了他一眼就收回視線。 他從筆筒裡抽出一把前幾天夏日祭拿到的扇子丟給他,「覺得熱就用這個頂著吧,誰叫某人懶到連自己爬起來去搬個電風扇都不肯。」 「我那哪叫懶!既然阿治你也覺得熱,那你就去搬不行嗎。」 「我說我沒有覺得熱。」 「是喔⋯⋯」宮侑再次懶洋洋地拖長了尾音。宮治這次光聽他的語氣就知道他打著什麼壞主意,他看著宮侑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輕盈往前兩步跨上他的大腿,雙手繞上他的脖子再把他熱呼呼的嘴唇湊了過來。 宮侑溫熱的呼吸打在宮治的皮膚上,毛茸茸的腦袋埋在他的頸窩裡亂蹭一通,搞得他有些癢。 「⋯⋯侑,你想幹什麼。」 「我在想要做什麼才能讓你這個蠢屁股熱起來幫我去拿電風扇啊。」 宮侑故作無辜地歪著腦袋。他的雙胞胎兄弟頂著一張跟他幾無相差的臉說出這種話,倒不會讓人感到有多古怪──儘管他們再怎麼像,宮侑會做出來的表情和說出來的話都不一定是宮治會做出來的表情和說出來的話,這點只要熟悉他們的人都知道。 但是如果──如果他們真的心血來潮想假裝成另一個人,或許還是可以蒙騙過對他們所不熟悉的大多數人。 現在宮治坐在這裡,他在想宮侑會做出來的某些事或許他還是沒辦法辦到。不是不能,只是不想。他沒辦法理解侑──他們兩個如果面對面,就像是一面鏡子分開來變成兩面。鏡子要在玻璃背面塗上水銀才能夠反射出鏡像,他們沒辦法看見的地方就是彼此的水銀。 侑一邊貼在他耳邊這麼說一邊黏糊糊地咬他的耳朵。其實根本不必他這麼做,宮治本來就覺得很熱──跟天氣大概只有那麼一絲半點的關係。侑在家裡時從來都不肯好好穿衣服,或者該說不肯好好穿他自己的衣服──他有一半時間會拿宮治的衣服來穿,另外一半時間就會像現在這樣,穿著無袖背心和短到不行的運動短褲,袒著整片光滑的大腿,只差沒直接露出屁股蛋來。 他的雙手繞在宮治的頸子上,呼吸從宮治的頸側移動到他的臉頰,沿著顎骨的線條把嘴唇湊了上去。宮治任由他的舌頭在自己嘴巴裡毫無章法地亂掃一氣,手掌從他寬鬆的下襬鑽進去。侑的皮膚上一層薄薄的熱汗,摸上去又滑又燙。 「嗯、」侑故意貼在宮治嘴唇上輕輕地喘,把熱熱的呼吸都噴進他的嘴巴裡。宮治咬住了他的舌頭,把那厚實溫熱的軟肉往自己的嘴巴裡拖,宮侑從喉間發出來被驚嚇到的氣音。 「阿治唔、嗯唔!」宮治認真起來時總是弄得好像要把人吃掉一樣。當他一手托住宮侑的後腦勺一手掐住他的大腿啃上去,宮侑幾乎快要不能呼吸,好像自己瞬間成了雙胞胎兄弟放在盤子上的一塊魚肉,要被連皮帶骨地咬下吞進肚子裡去。 他好不容易從宮治嘴裡把自己的舌頭解救出來,不及吞嚥的唾液將嘴角弄得濕漉漉的一片。宮治的手已經從他後背移到他的前胸,掐著那兩顆軟綿綿的乳頭,用指腹和指甲聯合擠壓著肉粒往裡面摩擦。 宮侑沒有料到自己只是撩了宮治一下能撩出這麼大的一團火來,敏感得縮起背脊的同時又驚慌地想要逃跑。不就是想吹個電風扇而已嗎?他想說話但是宮治此時已經把兩根手指都塞進他的嘴巴裡,宮侑不敢咬下去,軟軟地發出一聲低吟。 「不是說要讓我熱起來?」 宮治開始咬他的脖子。他對認定屬於自己的東西有這種脾性,喜歡留下自己的痕跡,用油性麥克筆寫上名字、故意扯出一部分的線頭,或者在肉眼可見的地方咬下一口──反正有人問起總是可以藉口他們在打架時也用上了嘴。儘管侑臉上的表情經常會出賣他自己,但只要宮治表現得足夠鎮定,沒有人會真的意識到異狀。 或者真的說出來。他們可是兄弟啊,還是雙胞胎。他們不可能會這麼做吧──但宮治就是在他們的眼皮下這麼做了。這點總是讓他感覺很好,但宮治不會老實承認──他和宮侑在這方面有著出自同套基因組成結構的彆扭。 侑還在試著想推開他的腦袋,「那也沒讓你咬我、唔,阿治!」他叫了一聲。宮治把他的上衣掀起來,順著鎖骨的線條咬上他平坦的胸口。宮侑的胸口摸起來沒幾兩肉,至少那手感就不及宮治的來得好。他打從心裡討厭宮治雖然和他長著幾無相差的臉和身材和身高體重,但他就硬是比他高了零點幾公分還重了零點幾公斤,儘管那微小的差距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宮侑眼中那從來都不可以稱做什麼忽略不計。狐狸的心眼向來很小而金毛狐狸的心眼更是小得要命,連把線穿過針眼那樣的大小都辦不到。 在他大半的人生裡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證明自己比宮治還好、跳得還高、力氣更大,更強壯更厲害。他知道自己在托球上贏過宮治(這點他再確定也不過),但他總是── 「⋯⋯嗯唔!」宮侑喘了第二聲。然後是接連不斷的好多聲。宮治的手輕而易舉地鑽進他寬鬆的繫帶短褲裡,鬆緊帶被手腕扯緊將布料撐起曖昧的弧度。他熱得連屁股也悶出了汗,現在那滿布汗水的兩片臀肉被雙胞胎兄弟的手掌抓捏著,揉成各種色情的形狀,兩根手指分開股間的縫隙伸了進去。 「這麼軟了?」 宮治低聲問。侑的臉皮脹紅了,伸出手去用力掐了他的耳朵好幾把。 「你就不能閉上嘴?」 「那你能不能也別這麼色。」 宮治反唇相譏。他的手指在宮侑屁股裡咕嘰有聲地攪了好幾圈。宮侑整個人趴在他的身上,原本貼著地面的腳掌現在腳尖繃起小腿伸直,被頂上前列腺時他一口也咬在宮治的脖子上。 宮治把自己的短褲扯下來,脹硬的柱體貼上宮侑濕漉漉的臀縫。 「侑,你知道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感覺不那麼熱嗎?」 宮治的皮膚現在感覺起來還是比宮侑自己涼一點,他難受地往宮治身上亂蹭一通,蹭得治整個人火氣都上來了。他單手掐住他的腰,一手扣住他的大腿,從腿根摸上去到肚臍下方,宮侑那根東西同樣硬梆梆地抵著他的小腹。 「嗯⋯⋯?」 他從鼻腔裡發出一聲氣音權當回答。宮治也不在意,他知道那聲鼻音代表「我現在快爽死了但還想要你插進來但我不想講但如果你接下來三秒內再不插進來我會開始扯你頭髮」,於是他讓翹硬的莖身抵著侑的股縫滑動了兩下,然後插了進去。 「只要讓自己熱到再也沒辦法思考自己為什麼那麼熱不就行了。」 ⋯⋯什麼歪理啊。如果現在宮侑還有一絲半點清醒的意識他會嗆他,但是宮侑和宮治在一起時經常沒有多少那種東西,或者理智,或者其他別的什麼。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就像氫氣遇上氧氣,或者像他們在實驗課做過的那樣,把放在燒杯裡的金屬鈉滴上一滴水,它們就會自己燃燒起來、生熱並且爆炸──侑不知道自己該是氫氣、氧氣,鈉或者水。或許他們四者皆是,他們都是彼此的氧氣。 現在他腦中唯一剩下的想法就只有這張椅子大概真的太小,宮治抱著他的腰肢聳動起來時還會發出嘎吱嘎吱的不堪重負的聲音。然後還有自家兄弟的那根真的熱得要命、真的,那樣的熱度和硬度宮侑心想那絕對是不太正常。他被操得背脊繃緊腳趾抽縮,汗濕的脊柱中線被對方用涼涼的手指上下滑動,弄得他只想扭身躲開卻被抓住頂得更深。 「嗯⋯⋯唔!阿治、」從額角滑下眉毛、再經過下頷線的汗珠被宮治用舌頭舔掉,再送進他的嘴巴去銜住他的舌尖。那根滾燙的玩意粗魯地破開深處的軟肉插到最底,途經的褶皺被完全撐開,雙腿只能軟綿綿地分開去承受對方恣意的侵犯。侑沒辦法抵抗那些,意圖抵抗宮治就像是抵抗一切他生來就有的生理反應,他對排球的愛或者其他別的什麼。 宮侑被操得腦袋發暈,性器抵著宮治的腹肌摩擦,沒有經過多餘碰觸就把精液噴在他的小腹上,留下微涼的黏答答的一灘。他感覺自己整個人都被浸泡在汗水裡,還有從他身上所有毛細孔、他的眼角和嘴角、他的半軟下的陰莖鈴口以及其它他不知道的地方所分泌出來的液體。 宮治在他的屁股裡以及嘴巴裡都攪弄出了水聲,宮侑已經熱到快要忘記「熱」這個字要怎麼寫。他摟著宮治的脖子在他身上黏黏糊糊跟隻沒有自我意識的小狗一樣亂啃一通,一個一百八十幾公分的高中男生在他兄弟身邊時總會降智成只知道不顧後果地亂吠挑釁、或者不顧形象地渴望身體接觸的軟體動物。宮治認定他是在撒嬌,但是宮侑會猛拐他一肘子,然後欲蓋彌彰地大喊我才沒有。 ⋯⋯啊,但是明明就有。他射進宮侑屁股裡時宮侑把他抓得更緊了,宮治恍惚間還以為自己被一隻深海裡的八爪章魚給纏上。他黏呼呼地靠在他耳邊喘息,黏呼呼地要跟他接吻。宮治接住他胡亂鑽過來的又軟又燙的舌頭,感到宮侑在他身上同樣軟成了溼答答熱呼呼的一團混亂。 他在把宮侑半拖半抱進浴室去洗澡(還先幫他套上了褲子)時還以為宮侑已經睡著了,畢竟那跟吃飽喝足的狐狸一樣懶洋洋半瞇起來的眼睛看起來簡直就跟睡著了沒兩樣──但他把宮侑塞進浴缸裡然後往他身上澆水時對方就醒了,然後他盯著正在把自己套頭T恤往上脫褲子也往下拽,準備把被弄髒的衣服過一過水再扔進洗衣籃裡的宮治時,突如其來說了一句。 「⋯⋯阿治。」 「嗯?」 「幫我剃毛。」 「⋯⋯」宮治的動作停了下來,「先不管你是從哪得來的主意──我們家哪有東西可以幫你剃毛?」他皺起了眉頭先把衣服扔在一旁,然後拿蓮蓬頭往自己身上隨便沖了沖,當成洗了第二次澡。 「難道你要拿爸的刮鬍刀來幫你剃?」 「我有買。」侑突然間又看起來很清醒了,他朝馬桶的方向努一努嘴巴,「放在架子上的衛生紙後,不信你去翻。」 宮治還真的去翻了。他從架子上那些雜七雜八的物品後撈出一包東西,用半透明的塑膠袋包著,看起來相當可疑。 他從裡面拿出來一把剃刀和一罐除毛軟膏。 「⋯⋯」 他扭頭看向宮侑。侑的眼睛閃亮亮地看著他,於是宮治不知為何很想要嘆氣。 他從骨子裡(大概是從侑身上分來的另一半血脈)知道對方的天馬行空大概都是其來有自,但卻依舊無法使人理解──而宮侑向來是屬於在這方面格外有行動力的人。 他說,「侑,你就真有覺得那麼熱?」 宮侑說是。 於是宮治就真的幫他剃了──他讓宮侑坐在浴缸邊上,分開兩腿。侑的那根東西剛剛才射過兩次,現在軟趴趴的,垂在深色的毛叢中,宮治把那遮擋視線的玩意從他腿間撥了開來。 「可別硬啊,侑。」他說,揮了揮手中的剃刀。 一股莫可名狀的戰慄從頭滾下侑的背脊。當他被耳提面命不能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就越是想要去做──他的大腦如此,他的身體也是一樣。 宮治開始給他抹上除毛膏的時候宮侑果不其然理所當然地在他眼前勃起了。他挑眉看他一眼,侑扭頭過去不看他但是耳根到頸線一帶的皮膚很紅,他咬牙又把視線轉了回來。 「⋯⋯我又不是故意的。」 宮治彈了他的性器一下,「看來你的身體是故意的。」 「我又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對我勃起?」 「⋯⋯」宮侑咬住嘴唇瞪他,「那你就不能別看?」 「我不看要怎麼剃?」 「唔⋯⋯」 未來即將成為廚師(但是侑還不知道)的手指靈活細緻,穩妥地在那團被水浸濕的毛髮根部塗滿綿密的除毛膏,像在給一塊烤過的麵包塗上濃濃的美乃滋。侑喜歡這種吃法,治則是喜歡塗上奶油的。 冰冷的刀刃貼上柔軟腹部的皮膚時讓宮侑敏感地倒縮一下。 「⋯⋯刮到你我可不管。」宮治抬眼看他。 侑小心翼翼地揪了一把他的頭髮,「那你就要負責。」 「負什麼責?」 「全部的責。」 「⋯⋯你這麼貪心,你媽知道嗎?」 宮治的聲音裡聽不出來是很平靜還是隱隱有些笑意。但侑聽得出來。 「明明也是你媽。」 「那你想讓誰知道。」 「你知道不就夠了?」 雖然嘴裡說著「我可不想一輩子拖著你這個大麻煩」,但是宮治手上的動作迅速又穩定,幾下就俐落將那些原本就偏稀疏的毛髮先用手指捋順了,再拿剃刀貼著與皮膚隔零點幾公分的縫隙將毛髮除去。侑的一條腿張開靠在浴缸邊緣,另一條腿的膝蓋輕輕抵著宮治的肩膀。他硬得有些發痛,大腿內側的肌肉很敏感地一抽一抽。他在宮治跟母親學做菜時就見過他拿刀的樣子,可是── 宮治臉上專注的表情讓他心裡有種古怪的感受。他在廚房裡見過他那種表情,在他吃飯時也看過,但他想不起來自己是否在排球場上看見過他這副模樣──治只會對他真心喜歡的事物露出這種表情。他想起青年隊集訓前他對自己說過的話。宮侑認為他的確也對排球露出過這種表情,他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自己是否看見過。 他的心臟困在肋骨間猛地跳了一下。他沒辦法去想那些事情。他的小腿貼在宮治的胸肋上,宮治的心跳是否能跟他一樣──宮侑不想去想那些事情。那種事情讓他心情不好,讓他很想砸壞什麼東西。 他垂眼看著宮治在他眼前的銀灰色的髮頂,中間一個小小的深黑色的漩。侑的手指悄悄爬進那些頭髮裡,宮治剛剛也出了汗,頭皮摸起來還濕漉漉的。 宮治抬頭看他一眼,「⋯⋯侑?」 他把剃刀放在一旁洗手台上,伸手摸了摸自己剛剛剃過的那片皮膚,又拿過蓮蓬頭來給他沖水。 「癢死了。」 宮侑輕輕地踢了他一腳。宮治抓住他的腳踝,伸手在他依舊堅挺的那根東西摸了摸。 宮侑的那條腿於是自然而然掛上他的肩膀,理所當然地這麼說,「治,幫我舔。」 「你剛剛都沒幫我舔了,還要我幫你舔?」 「那我等下再幫你舔嘛。」 「⋯⋯你就這麼想讓我舔?」 「那你舔不舔嘛。」 宮侑拿腳趾頭去撩宮治的背脊,又從他的脊柱滑下他的腰側,最後抵在他的小腹處輕輕地磨。宮侑連腳掌跟腳趾頭也會記得抹上乳液,觸感柔軟又細膩,熱呼呼的腳心抵著宮治的胯下磨蹭,很快就把他從半硬磨到全硬。 宮治沒動,只剛剛握住宮侑性器的那隻手有一搭沒一搭地拿拇指摩擦剛滲出清液的鈴口。宮侑在他手掌下輕輕地抖起來。 「阿治⋯⋯」 他的尾音更軟了。本就黏糊的關西腔現在更讓他像嘴裡含著一顆棉花在說話,或者含著一顆跟他的眼珠子一樣色澤味道的糖。宮治感覺口舌發乾但是那毫無理由。宮侑總是能夠讓他毫無理由。 宮治低頭把他含了進去。 現在宮治想起來時,他只能想到嘴巴裡都是宮侑的汗水、精液,還有其他亂七八糟的體液的味道。他把宮侑的後脖頸扣住吻了他,宮侑也把他的精液嚥了下去。宮治有那麼短暫的一瞬間想把他連皮帶骨吞進肚子裡去。 他心想這種感覺只要宮侑在他身邊時就從來不會少過幾分。 「我聽說剃毛之後不穿內褲不會比較舒服。」 「⋯⋯是嗎?」 宮侑的身體貼在他的身上,他的手摸上了他光溜溜的下體。更衣室裡沒人,宮侑的褲子裡也沒有除了他的手掌以外多餘的其他物品。宮治的眼角餘光盯著宮侑透紅的耳朵尖。 真是莫名其妙,宮侑心想,為什麼他好像還是覺得很熱。 「⋯⋯結果網路上說剃了毛會比較不熱根本一點用都沒有嘛。」 「你說什麼?」 宮侑含在嘴巴裡嘟囔的字句沒有讓宮治聽清,於是他憤憤地又咬了他的脖子一口。 「明明還是熱死人了。」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