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解在冬季的花火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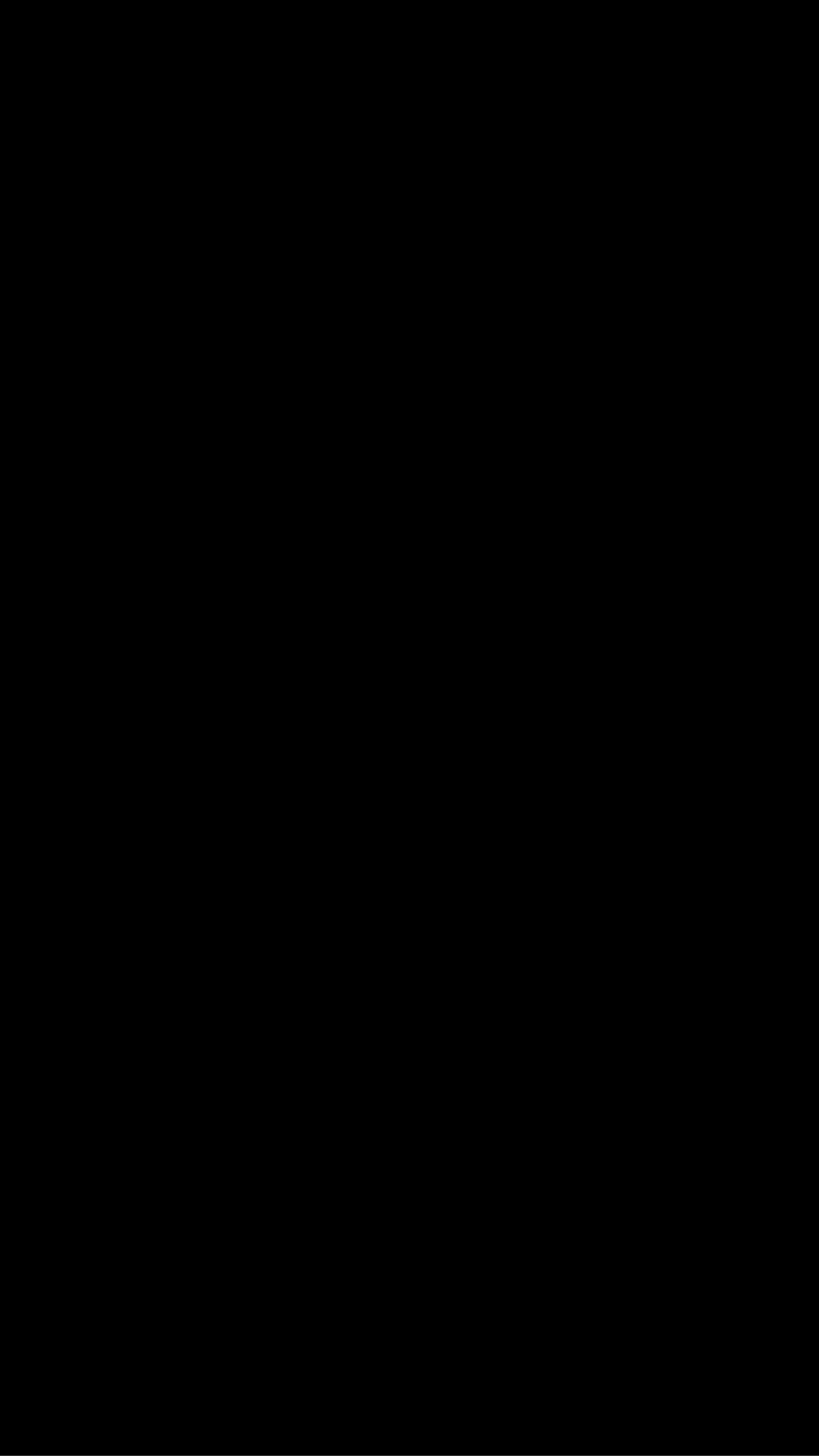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1日
- 讀畢需時 11 分鐘
今年的冬天來得太過突然。
夜久搓著自己的手,趁著還沒冷卻之前放進大衣的口袋,也不曉得是什麼巧合,被人潮沖散的部員們只有黑尾和他撞在了一塊。黑尾一直都是未雨綢繆的人,在寒流來襲之前就備好了羽絨衣掛在部活室的櫃子裡,今天也是,到了晚間才驟降的溫度,黑尾早已備妥一雙防寒手套,雙手不畏寒冷放在外頭,和周圍低著頭、把臉塞在圍巾裡的人們大不相同。
也和冷得把自己縮成一團的夜久完全不同。
即使祭典裡的人潮多得擁擠,夜久仍然不覺得溫暖到哪裡去,他不著痕跡往黑尾的方向靠攏了點,也許只是半步的距離卻稍稍溫暖了些。
心理作用吧。
盯著黑尾寬厚的背影,雖然平時總愛和黑尾鬥嘴但其實自己算是很依賴對方,即使是現在,他也是靠著黑尾放慢的步伐才能這樣不疾不徐跟在黑尾後方,黑尾的溫柔體貼總是默默不語,像是寒冬裡輕輕為其披上的一條圍巾,既不沉重又足夠暖心。
夜久憶起春高的東京代表決定賽,因意外而受傷休養的那幾天,黑尾難得什麼挖苦的話都沒說,只是靜悄悄地待在他的旁邊,放學後也沒有和研磨一起回家,而是和他站在同一邊的月台,直到看他上了電車才隨口說了一句「明天見」。
夜久沒有問黑尾為什麼,也沒有趕黑尾走。以往都覺得他刻意的溫柔是另有目的,那一次卻不可思議地感到安心。
隔天早上,夜久在學校那一站的車站門口看見黑尾手插著口袋等他,嘴裡說什麼「要遲到了」順手搶走他的書包,開玩笑,明明都搭了比平常還早的電車,怎麼可能會遲到?夜久來不及回嘴便看見黑尾朝他伸出一隻手,漫不經心地再次開口。
「樓梯有點陡,還是你要搭電梯?」
「……我又不是重傷患。」
沉默數秒後,夜久這麼回應,但是手仍然搭上了黑尾的掌心,因為他感覺縱然無視黑尾,黑尾還是會來拉住他,到時候不論是接受還是拒絕都會很尷尬,不如早點接受這份好意。
手裡的溫度在入冬的此刻顯得特別溫暖,厚實的手掌多了幾顆水泡,最近的黑尾是有些練習過度了,或許是為了在緊急時刻能更加從容的應對,但追根究底那一次是他沒有留意球的落點,顧著追球才會落得那種下場。要是音駒輸了,即使沒有半個人會說是他的錯,他也肯定難辭其咎。
山本也是、黑尾也是,他們都不會原諒自己。
所以那一次,他想跟黑尾說聲抱歉、也想說一句謝謝,他把至今攬在他們身上的責任全都讓黑尾一個人背負,而黑尾完美地帶領隊伍贏下勝利。
——對不起啊,謝謝你。
這麼想著的夜久不自覺捏緊了交握的手,黑尾回過頭,一句話都沒問就放慢了腳步。
……笨蛋,不是因為你走太快才捏你。
夜久抬眼看了黑尾一眼,黑尾挑起眉似乎在考慮是否該走得更慢一點,在黑尾得出用揹的比較方便之前,夜久移開視線低喃了一句謝謝。他不知道黑尾那時候是用什麼表情回應,但是後來幾天黑尾都是用這樣慢悠悠的速度和他一起上下學、一起換教室,直到醫生說可以正常練習之前,黑尾都沒有拋下他。
夜久早已了然於心,那才不是什麼心理作用。
於他來說黑尾鐵朗是特別的,是那種僅僅只要站在那邊就令人安心的存在,焦躁的心情會在瞬間平復,每一口呼吸都能聽見自己漸趨平緩的心跳。就像球場上最緊張的時刻,當黑尾跳起的背影映入眼簾,夜久就能預見球的落點,當黑尾回頭與他擊掌,掌心的熱度似乎就要蔓延到頰邊,他不曾在乎過這種熱得發燙的心情是什麼,但確實除了黑尾以外沒有人能讓他有這樣的感受。
他不曉得該如何定義黑尾在他心中的位置,姑且就將他擺在了隊友之上、朋友之上,比海信行再高一點點的地方。等到發覺的時候這種無以名狀的情感已經發酵,以無法遏止的速度悄然擴大。
/
黑尾早就預想到祭典會有很多人參與,也許會有人被沖散,所以一開始就和大家訂好了集合的地方,但是他想也沒想到自己會和夜久兩個人沖在一塊。
不,這不是什麼巧合,想想稍早踏入祭典那時,他的視線就一直落在夜久的身上、盤桓於後頸那若隱若現的膚色。他不曉得大家是什麼時候被沖散的,只知道回過神來就剩下他們兩個,黑尾跨大步伐走到夜久的前方,主動為夜久疏通前方的路還細心地緩下腳步,好讓夜久跟上他的大長腿而不落單。
——要是這麼坦白,夜久絕對會生氣,所以黑尾做得小心翼翼,畢竟現在的夜久並不需要靠他也能好好跨出每一步。
他並不是特別想為夜久做些什麼,只是春高地區賽看到夜久受傷離場的時候,才有一種夜久可能會離開他的錯覺,不,他在想什麼呢?不只是離開他,而是可能離開球場、再也無法並肩作戰的恐懼湧上心頭。
夜久再怎麼強大卻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妖怪,他比場上任何一個人都更了解這件事。眼睜睜看著夜久飛越擋板,比起那注定被接起的球,他更在意夜久爬起身時一閃而逝的扭曲表情。
確認球落地之後,他幾乎在第一秒就衝了出去。壓抑在心底的恐慌顫抖著擴散四肢百骸,在夜久那張快要淚崩的不甘心之前,黑尾收緊了五指敲敲自己的胸膛,他死也不會在夜久面前表現出脆弱的模樣,從見面那時起直至今後,他會成為守護神歇息時的肩膀,絕對不會讓夜久的離場成為音駒的漏洞。
所以——黑尾望向夜久——你就安心看著吧,然後為了下一場比賽好好休息,早點回來與我並肩。
後來幾天,其實大家都想要陪著夜久一起回家,但是山本的表情太糟了,雖然那一天有振作起來十分了不起,不過現在面對受傷的夜久,那表情絕對是零分。於是黑尾拒絕了,不只山本,所有人他都幫夜久婉拒了,說著「夜久不會想讓後輩們同情」這種爛理由支開了隊員們。
他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只是在看到研磨那彷彿心知肚明的表情突然有些心虛,啊啊,幼馴染就是令人討厭,尤其研磨擅長察覺連他都未必了解的自己,用著打趣的眼神期待接下來的發展。
他才不想問研磨這份心情是什麼,不想從研磨那裡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想和夜久獨處,這不該是從他人嘴裡發覺的事情,他不由得這麼想。
/
祭典的煙花向上升空炸出一片燦爛,四周隨之響起震耳歡呼,黑尾和夜久還來不及從人潮擠出,煙花大會便開始了。
黑尾掩著一邊耳朵,眼角瞥見要被擠開的身影連忙抓住了對方伸出的手,輕巧使力將人帶到自己身前,夜久一個踉蹌險些撞上黑尾的胸膛,稍微緩了一口氣,抬起頭時正巧迎來下一波璀璨,彼此的半邊臉被光芒映得耀眼,金色眼瞳彷彿有什麼寄居其中惹得夜久心頭一熱,想抽回手卻被抓得牢固。
「牽著吧,以免走散。」
順勢將夜久的手收進大衣口袋,黑尾不自然地扭過頭轉移視線,夜久也同時收回目光,幾步挨近黑尾的臂膀。
毛絨手套沒一下子就將口袋變得暖烘烘,胸口跟著熱了起來甚至於有些難受,即使呼吸困難,夜久仍是貪圖黑尾的溫柔,不願抽離那溫暖的所在。
煙火持續綻放將夜晚的星空照得宛如天明,在停滯的人潮中他們沉默前行,漸大的歡呼聲昭告煙花秀即將迎來高潮,興許是趕不上約好的集合時間,興許是他們都留戀於彼此的溫度,倆人不約而同放緩步伐,企圖拉長獨處的時間。
掌心好熱。
黑尾一刻也沒放鬆力道,像是要禁錮夜久一樣將他鎖在手心裡,腳傷的時候也是這樣不容拒絕的力道,就算夜久不想依靠他人,黑尾的肩膀也會自己擠過來讓他靠上,不知不覺那雙臂膀成了夜久的避風港,在他需要的時候黑尾一定都會在,似乎已經是理所當然。
夜久仰首望著熱烈的五光十色,在那樣斑斕的色彩下他注視著黑尾端正的臉龐,光芒落在他的眼底、跳動的心不受控地加速,似乎就要明白這股熱度的意義。
「啊……喜歡……」
覺察的時候連夜久自己都感到錯愕,無意間出口的兩個字被周遭的人聲淹沒,顧不上遮掩自己泛紅的面頰,是因為黑尾回望他的表情同樣帶著難以形容的悸動。
「你剛剛說了什麼嗎?」黑尾微彎背脊,溫熱的白煙模糊了彼此距離。
「沒、什麼都沒有。」
「是嗎?」
黑尾歛下眼眸,視線停留在夜久冷得發紅的鼻尖,再往下是微微抿起的唇瓣,想要獨處的理由、想要一直看著夜久的理由在此刻並不重要,他只想知道如果不走出人群,握住的手是不是就能一直牽著?
他能不能將夜久永遠綁在身旁?
「幹嘛?」
側過頭,夜久的眼神不自在地飄向他,從下方抬眼看他的視線令心臟漏跳了一拍,明明與平常的角度無異,怎麼就令人緊張得要喘不過氣?黑尾短促地倒抽一口,在夜久疑惑的目光下將人拉往另一個方向。
「欸?你要去哪裡?不是約好去河堤——」
「現在去也來不及了,我知道另一個可以清楚看到煙花的地方。」
「還不是你走路慢吞吞……」
漸弱的聲音毫無底氣,黑尾笑瞇了眼睛,誰也沒有指出夜久同樣放慢了步調,他們挨著彼此穿越擁擠的人潮,過了攤販之間的狹小縫隙後再爬上一段石階梯,撥開樹叢之後可以看見有個小小的平台,從這邊能看見下方密密麻麻的群眾以及天上那綻放的火光。
「歡迎來到我的秘密基地!」黑尾張開雙手熱烈地說道,夜久環視一圈後禁不住調侃。
「什麼都沒有的秘密基地?」
沒有椅子、沒有玩具、沒有遮風避雨的屋簷,和他小時候與弟弟們用窗簾、木板搭起的小屋可說是天差地別。
「有什麼關係?基地只要有兩個人就能成立。」
「什麼歪理,那你之前是跟誰來這裡才有了這個基地?」
黑尾衝著他一笑,夜久才覺得這問題是白問了,小時候的秘密基地肯定只有研磨這個選項,要是一開始就約在這個地方他們大可不必人擠人,還讓他察覺了沒有必要知曉的心情,話說回來真不該答應黑尾來到這裡,他害怕自己一個不小心沒有藏好表情,會被黑尾這個心細的傢伙看出端倪。
黑尾三兩步回到夜久跟前,褪去了那雙絨毛手套,嬉皮笑臉地給出解答:「這裡是在這一刻成為我們的秘密基地!」
「哈?」
趁夜久怔然的時間,黑尾拉起被寒冬吹凍的雙手,稍早被他握在口袋裡的那隻手還留有暖度,另一隻則是冰得令人心疼,他用雙手包覆住夜久小了自己一號的手,像揉暖暖包那樣輕輕地搓呀搓。
夜久圓睜著眼一時間反應不及的模樣令黑尾忍不住想笑,就算人聲再怎麼沸騰他都不曾聽漏夜久的聲音。
「你說你沒有說話,所以我就先說囉?」黑尾停頓半秒,在對上夜久抬起的目光時脫口而出:「我喜歡你。」
這句話突如其來地在夜久心底投下震撼彈,嘴巴一張一闔理不清自己該做何反應,前一刻才知曉的心意下一刻就收到了回應,他該坦率點說句「我也是」嗎?一片混亂下他吞吞吐吐支吾其詞,這一點也不像自己。
「那個、啊……抱歉。」
「咦?」黑尾一愣,尷尬瞬間染紅了整張臉。
為什麼要道歉?
黑尾那顆聰明的腦袋快速運轉著,難道是他聽錯了嗎?還是說夜久是在談論哪個路過的美女?又或者那句喜歡是在講旁邊攤販的炸肉捲?
啊啊,對啦,那的確很香,他聞到孜然的香氣時也感到餓了,何況那還是夜久最愛的肉類料理,是他不對,不該拖著夜久繼續走的,夜久那時候是想買幾份帶去河堤吃的對吧?
自己真是蠢到家。
戀情才沒那麼容易開花。
「不,我才要抱歉,這麼突然……」
望著裹在手裡的小巧雙手,無法用纖細來形容這雙充滿磨練的手,這雙手無數次托起希望,在眾人回頭的時候,以毫無破綻的姿勢散去扣殺的衝擊,那顆藍黃相間的球在燈光籠罩下回到舉球員手中,然後他會開始助跑,用所有的力量回應那完美的一傳。
夜久是音駒的守護神,亦是王牌。儘管如此,這雙手他輕而易舉就能包覆,名為勳章的傷痕此時是多麼令人憐惜。
他無法放開這雙手。他知道、自己應該立即拉開兩人的距離,但卻醉心於夜久的溫度、希望能獨佔他的氣味,在冬季的寒風之下他想將所有的溫暖奉獻給他。
「黑尾……!」
壓抑的叫喚拉回黑尾的注意力,一抬眼,對上一張面紅耳赤的臉,平常時候他會勾起嘴角笑他,說「阿夜你是在害羞嗎?」然後不甚在意地強拉著人去做這做那,或是說句「開玩笑的你當真了嗎?」將這件事情強行回歸原點。
對,沒錯,他想。是該回歸原點,現在說什麼「開玩笑的」肯定是來不及了,他也不想把這件事當成一個無趣的玩笑,那麼、就從追求開始吧,誰說夜久不會回頭喜歡上他?
「我是認真的,你可以……」彷彿被夜久的窘迫感染,黑尾哽著一口氣,用深呼吸化解胸口無解的難受,「……你可以慢慢考慮。」
黑尾的認真透過手勁一股腦傳遞給夜久,明明陣陣吹來的風還是那樣刺骨,手腕卻宛如要被融化似的燒得他無所適從,起初夜久是想抽回手的,然而黑尾卻沉默地凝視著他的雙手,他不明白黑尾彼時在想些什麼,只覺眼裡的熾熱好像透過血液直衝他的腦門,幾乎抽走了他反抗的能力。
那神情不久前他也見過,受傷的那段時間黑尾也常常用那樣的表情望向他扭傷的腳踝,夜久會下意識遮掩那道視線,原本以為是同情,但事實上並不是那種廉價的意義。這雙手是排球選手最重要的生命,這雙腳亦然,而黑尾彷彿想要替他守護包含生命的一切,緊緊裹住他凍僵的指尖。
好不甘心,稍不注意就要落入黑尾柔軟的圈套。
在黑尾倉皇地鬆開手時,夜久沒多想就捉回了那雙比自己大上一圈的手腕。
「不用考慮了,雖然不是很想承認但我——」
意識到之後,這句話變得難以啟齒,為什麼黑尾能夠若無其事地告白?要是稍早可以藉著黑尾的勇氣一個勁地表白就好了,如今由自己開口就莫名難為情。
夜久一直是個行動派,說不出口的話用行動代為表達就好,這是兩情相悅,他迫不及待想告訴黑尾。這一份焦急導致拉扯黑尾的力道是大了點,多餘地想著黑尾該不會生氣吧?夜久一雙唇貼上了彎下背脊的黑尾唇邊。
原本目標應該是臉頰,但黑尾彎腰的幅度不夠他只能貼在靠近唇角的地方,不過這樣子也比較能表達「喜歡」的意思吧?
貼近的時間不是很久,打斷他的是天上綻開的花火,夜久這才發現煙花大會還沒結束,像是剛剛他們談話的時間全靜止了一般。
「……我可以解釋成這是『我也喜歡你』嗎?」黑尾低啞的聲調蓋過了遠處煙花的聲響,夜久一恍神,視線落在黑尾歛下的目光。
「嗯,可以。」
「那你為什麼要道歉?」
「因為……事出突然,我還搞不清楚也有點混亂所以、唔……!」
冷不防被扣住了後腦,黑尾熾熱的掌心緊緊摟住夜久的後腰,迫使他踮起腳尖淹沒在黑尾滿是情意的長吻之中,他抬起臂膀環抱住黑尾的肩,用盡全力回應。兩個人宛如兩隻餓昏頭的野貓,碰到美食就巴上去又啃又咬,他們交換了幾次呼吸才窒息般地分開彼此。
互瞪的模樣好似回到最初在部活室相遇的那一天,夜久也是這樣仰首看他,不同的是、他們的眼神裡不是當初的狠勁,而是難以言明的渴望,黑尾能探進那雙棕色眼瞳裡不為人知的情愫,而夜久肯定也同樣。
不經意望見自己咬出血的唇角,夜久抬高下巴搶先開口:「這次我可不會道歉!」
黑尾一怔,這才發現嘴邊有股腥甜的血味,在剛剛那樣的掠奪中他也沒有心力去留心力道,現在反而有點擔心夜久的腰是不是被他抓出了痕跡,但看樣子、夜久那件厚重的風衣或許替他分散了手勁。
望著眼前滿臉通紅卻又理直氣壯的夜久,黑尾好笑地搖頭。
「你從來都不需要道歉。」就像受傷離場那時候,夜久只是拼命過了頭,沒必要向任何人說對不起,不過、這一次或許該跟夜久要一點補償,因為受傷的人是他。
在一束細小的鳴響升起時,黑尾伸出手,光芒在他身後輝煌綻放。
「讓我牽你的手,我就原諒你。」
分不清是尾聲的煙花太過耀眼,還是黑尾的話語太過矛盾,夜久一時語塞,半晌之後不由自主伸手搭上黑尾翻出的掌心,當溫度溶解在一起,他便被拉進厚實的懷抱裡,溫暖得恍若春季來臨。
*
by 匿名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