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敵
- null nu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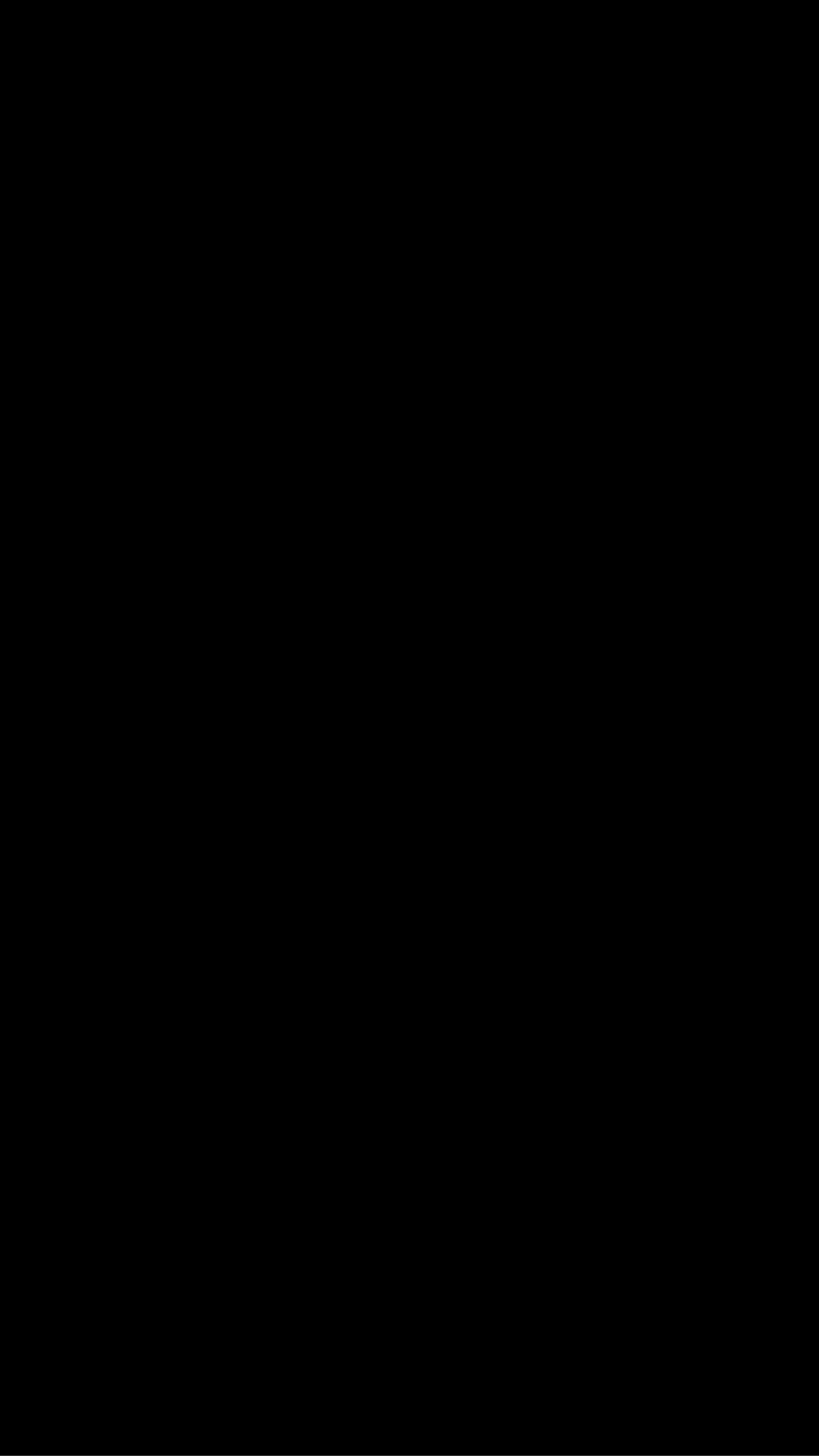
- 2022年3月11日
- 讀畢需時 9 分鐘
已更新:2022年3月12日
我們的春天止步於四分之一決賽。
那是我們第一次進軍全國。現在回想起來,那好像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收尾收得猝不及防,還沒反應過來,我們已經披著毛巾下場,成為從東京體育館消失的隊伍之一。
接續而來二零一三年的夏天更加漫長。高中聯賽的縣預選上,伊達工的鐵壁在一年後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牆,擋住了網對面的景色。
波折不斷,前路受阻。日向在這樣一個夏天裡決定了自己未來要去的地方。
*
下課鐘響,我拎起書包才剛起身,有個人影一溜煙竄到我的桌下。
我低頭和那團毛茸茸的橘色髮頂對望,輕輕踢了踢桌腳,「這次又是什麼?英語考試不及格,數學作業沒寫?」
日向蜷縮在課桌底下,兩手握著桌腳抬頭瞪我,「你就不能想一些和成績無關的可能性?」
他的話音剛落,班導喊著日向名字的聲音就從教室門口傳過來。
同時間日向用力扯住我的褲角,我防備不及,被他拉著坐回課椅上,一低頭看見日向祈求的眼神,讓我一下子把原本要罵出口的話全部吞回去。
不知不覺我們也站在了和當初大地前輩們相同的位置上,「未來的志向」從小學時候的作文題目真實地轉變為高三學生日常話題,連身邊的長輩師長都不時來關切。
我的進路相談還算順利,爸媽對於我打職業排球這件事沒有太多干涉,反觀日向的苦難好像從一三年的夏天後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看著藏在桌底一臉懇求的日向,砸著嘴撈過椅背上排球部的外套,用自己都覺得彆扭的演技趴回桌上裝睡,拿身體盡可能擋住桌子底下的可疑人物。
危機解除得很快,班導走到後排,看著空空如也的日向座位,嘆著氣又離開教室。
我還不敢輕舉妄動,眼睛睜開一條縫往外偷看,確定沒人了才完全起身。桌底下日向兩眼緊閉,雙手合十,活像個相信只要閉著眼睛你就看不到我的笨蛋。我挪著椅子往後退開,伸出腳踢日向的小腿,向他提示敵人已經走遠。
日向被我踢了幾下,皺著眉頭睜開一隻眼睛。他爬出來,揉著因為蜷縮的姿勢而痠痛的肩膀,姿勢不正地癱在我的課椅上。
「你今天不去社團?」我問。
「阿?要去要去。」日向呻吟著回答。
「那還不快走。」
「等一下啦,我的小腿很痛誒,影山君踢人好粗魯。」
一定是藉口,我根本沒出多少力。我不管他,拎起書包往教室門口走,果然日向迅速竄過來擋住去路,仰頭盯著我看,莫名一臉欲言又止。
「我躲班導並不是因為作業沒寫哦。」日向瞪大眼睛對我強調。
我愣了一下,罵他呆子,「我知道。」
很多人問過我日向為什麼要去巴西。
我自認已經不像小時候那樣遲鈍,和日向待在一起的整整三年,旁人會認為我們知道對方的所有事情也是理所當然。
我們的確經常討論很多事情,主要是排球的戰術,其次是作業和補考,再接下來是更多瑣碎到我也無法細數的小事。直到有一天我經過日向的教室,聽見日向的朋友喊他,翔陽又要去三班?除了上課以外你們到底哪時候沒待在一起?
那時候我才驚訝的注意到,我們所擁有的待在彼此身邊的時間,說不定比家人都還要長得許多。
可是唯獨未來的進路這件事我們沒找彼此討論過。我也覺得不需要,我去打職業,日向去巴西訓練,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目標,沒有什麼需要質疑。況且我們高一的時候就已經約好,要在世界的頂峰見面,日向沒說過要反悔,這個約定就應該還算數。
我們坐在搖搖晃晃的電車上,海在遙遠的鐵路另一頭,我的襪子底下還留有砂礫粗糙的質感。
幫日向躲過進路相談的那天,晚上剛到家日向的簡訊就踩著點傳過來,問我周末有沒有時間。
高二時我曾陪日向去過一次海邊,回家後第三天還總有沙子黏在身上的錯覺。初次會過大海之後日向更投入於研究沙排影片,相較於第一次的狼狽不堪,今天與大海的二次會面我們都早有準備,但技術與體力還是彌補不了過低的經驗值,我們在沙地上跌跤跌了個盡興,回程路上筋疲力盡地抵著彼此的腦袋打瞌睡,起來的時候脖子痠痛得讓人齜牙咧嘴。
下車前我們早已餓得不行,合意到站後先去坂之下買肉包,日向結完帳到外面等我,出來時我看見他握著紙袋,難得一口肉包都沒啃,直直盯著夜幕即將落下的天空。
我莫名想起剛才和日向在沙灘上的對話。
日向將褲腳捲到膝蓋,盤腿坐在沙灘上,任由一陣一陣的海潮沒過屁股和小腿,身體跟著輕輕地左右搖晃。
他瞇著眼睛眺望遙遠的海平線,突然問我,「你小時候有沒有想過,伸手就能摘到星星?」
「沒有。」我直覺回答。小時候我只想過怎麼跑贏姊姊,忙著和爺爺學跳發,要怎樣才能在球場上打更長的比賽,「我沒想過那些有的沒的。」
「真沒禮貌,什麼有的沒的!」
「但不可能吧,星星又碰不到。」我忽視他的指責,就算我成績再差也知道,星星不是什麼伸手就能抓到的東西。
日向扭過頭來看我,露出和之前擋在教室門口時同樣欲言又止的表情,似乎在醞釀想說的話。
「那我去巴西呢?」半晌後他說。
「啊?」我一時之間沒能消化問題,前後聯想,難道他是想問我覺得可不可能?
「不是要問你那些實際的,會不會成功或值不值得。」所幸日向很快為我解答,「就說關於這件事,你覺得怎麼樣就好。」
時間已經晚了,夕色之下,他的表情認真,不帶一點開玩笑的意思,但也不像是要徵求我的意見。海面橙色的陽光當作背景,日向渾身被反射的溫柔夕色包裹,襯得他整個人朦朧起來,好像連大海都為他撐腰,故意要讓我更加摸不清意圖。
我抹掉瀏海尾端凝結的水珠,放棄尋找也許根本不存在的正解,也放棄搜索具體又精準的詞彙,甩出腦中直覺冒出的第一句話,「……去得好。」
我敢說,日向筋疲力盡的原因之一,肯定是因為在聽完我的答案後,笑得在沙灘上滾成一隻像在泥濘裡洗過澡的迷你豬。
快到家時我看見日向的母親站在門前和鄰居說話。
我想上前打招呼,日向卻扯著我的手臂藏進旁邊的防火巷。兩個人擠在狹窄的小道,帶著海潮鹹味的衣服黏在身上的感覺很不舒服,我的背緊緊靠在磚牆上,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熱氣,低頭看到剛才因為情勢所迫而被我圈在手臂之間的日向。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見日向的睫毛,隨著他眨眼的動作搧動起來,近在咫尺。我徒勞地向後靠,想盡辦法讓自己離日向要命的體溫遠一些。
「哪裡不能打排球,為什麼要去到那麼遠的地方?」
一牆之隔傳來的聲音讓我們的動作同時停下來。
日向家的長子要去巴西這件事在街坊鄰居之間造成不小的騷動,這樣一個四面環山的鄉下地方,光是誰家的孩子到東京念書就能稱上大事,那麼巴西遠征的程度大概和搭太空船遠征月球一樣重大。
無論是進路相談的班導,或者是七嘴八舌的鄰居,他們的質疑都令人難解,在我看來,日向對於自己要去哪裡、該做什麼,兩者都清楚無比。
耳邊還聽得見鄰居的聲音,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翔陽為什麼要去巴西?犧牲那麼多,能保證夢想就會實現嗎?這樣追夢真的值得嗎?
我第二次想起日向在沙灘上拋給我的問題,和他聽完我的回答後笑出眼淚的眼角。
煮飯時鍋碗碰撞聲,寵物犬的吠叫和烏鴉的鳴叫,夾雜著鄰居此起彼落的關心。小小的鄉間住宅區熱鬧無比,顯得全程低頭的日向更加安靜。
天色已經完全暗下,我看不清日向的表情,礙於距離和姿勢,此時我不管做什麼動作好像都不太對。
困擾糾結了半天,我伸出雙手,分別掩住日向的兩邊耳朵。
在被我的手掌摸到的瞬間日向終於動了。他抬頭,臉頰的皮膚被我握在掌心,觸感柔軟,溫度滾燙,跟坂之下的肉包一個樣。
現在這顆帶著海水味的肉包在笑,用口型罵我是笨蛋。
外頭喧囂無比,我的手裡掌握著他的臉頰的生殺大權,日向還是一樣不知好歹,笑臉如常,好像沒有什麼能動搖他的好心情。
我突然之間鬆了口氣。
*
我等在公園前,沒多久就看到換下制服的日向推開麵包店的門,跑到紅綠燈旁朝對向的我揮舞雙手。
等他越過斑馬線來到我身旁,還順便帶來一身烘焙屋的香氣,把一個裝滿麵包的塑膠袋往我手裡面塞。
「這是讓影山小朋友等我的賠禮。」
我掂了掂重量,「太多了吧。」
「還包括下禮拜的份。」日向一臉正色地補充,「我要打工不能去送你,你不要哭啊。」
「才不會。」我用手指抓日向的腦袋,他難得沒躲開,只是護著腦袋抗議。
「你得對我好一點,東京可不會有人送你免費的麵包!」
這點我得同意。我放過他,老實地把麵包收下。
「我帶了排球。」我問他,「要打嗎?」
三年來日向對於類似的提議總是歡欣鼓舞,像聽到主人宣布吃飯的寵物犬。可這次日向卻突然露出肚子痛的表情,我不解地站在原地,看日向演完一段觀眾只有我一人的痛心獨角戲,艱難地對我開口,「下一次吧。」
我來不及說話,日向語氣鄭重地接著補充。
「下一次,在球場上見面的時候。」
我們之間的下一次總是間距很近,可能只是周末,甚至是明天。
下個禮拜我就去東京了,再接著輪到日向出發,日向正在存錢,沒事不會往東京跑,期間如果我沒有回宮城,今天就是我跟日向近期最後一次見面。
我人生首次在日向口中的「下一次」裡聽出了難以預期的遙遠。我不自覺地張嘴想多說點什麼,掏空腦袋也沒擠出半句,只能沉默地跟在日向身後進到公園裡漫步。
我們逐漸靠近公園中央的遊樂區,日向幾個跨步跳到原木裁成的平衡木上,展開雙手在狹窄的立足點上搖搖晃晃保持平衡,我不想看他摔倒,只好一步一步跟在一旁。
可日向不配合,他伸手把我拉上去,讓我們倆一起站在同一條窄路上。
他面向我,像小孩學步那樣倒退著牽著我走,走到一半我注意到日向在悄悄捏我的手指。他也沒打算藏,小聲地嘀嘀咕咕,「雖然剛才是我自己說下一次的,但還是,還是,啊——」日向深深地嘆息,像個老頭子一樣抱怨個沒完。
好想扣球啊可惡——笨蛋山——為什麼要拿這種終極二選一考驗我的意志?
「下次見面就可以了吧。」我理所當然地說。
日向依然專心地捏著我的指腹,「不行啦。」
「為什麼不行?」我對他語氣裡的傷感感到不滿意。
發現我的語氣認真,日向有點驚訝地看向我,「除非我也進阿德勒,不然我們就會是對手。對手誒,你打算給對手托球嗎?」
我在日向的質問下徹底空白。
「你該不會是忘記這件事了?」
「……」
日向咧嘴得意地笑起來,「看來影山選手也很想給日向選手舉球哦——你看,想啊想的都忘記這麼重要的事情了誒——」
「……日本代表。」
在日向得寸進尺說出更多氣人的話前,我終於反擊。
「只要我們都進日本代表,就沒有理由不可以吧。」
我執著地盯著日向,滿意地看著那雙橙色的眼睛越睜越大。這句話聽來狂妄,我們連下一次見面都遙遙無期,日向要去巴西,我去阿德勒,未來什麼都說不清,可事實就是事實,約定就是約定,連宇宙意志都無法輕易扭轉。
日向的鞋子尾端最終踩在了平衡木的盡頭,一動不動,還緊緊地抓著我的手沒有放開。他消化了老半天,眼睛狂眨,終於蠕動著嘴巴想說些什麼。我迅速反應過來,在日向開口前用虎口制住他的下巴。
幾番回合下我們跳下平衡木,一路絆著彼此的腳打到沙坑旁,眼看情勢危急,日向鼓著嘴掙扎起來,模糊地辯解,「不會再罵你笨蛋了啦,先放開我,要跌,要跌進去了!」
我在日向的再三保證下狐疑地鬆開手。他抹抹嘴巴,看了看四周,忽然踮起腳,往我的嘴唇啄了一口,然後迅速躲遠。
我愣在原地臉紅,上前把日向從遊樂區的圓筒裡拖出來。
「先說好,」日向的樣子也沒比我從容,他硬是裝出一副很自然的樣子,「不可以捏頭,再捏會變矮。」
「誰說要揍你了?」
日向的表情也狐疑起來,「那你要幹嘛?」
我還牽著他的手,吞吞口水,說,「剛才的那個,再一次。」
當日向第二次踮腳,我閉上眼睛,想到日向為我戴上毛巾做的王冠,想到我為他取的別稱第一次發亮的那一刻。
我能清楚記起日向在場上無數次的助跑,自願成為誘餌,成為得分的武器,他揮空之後原地落下,球從另一個角度越過球網,在對面場上砸出紮實的聲響。
扣球之後熱辣的疼痛突然出現在我的掌心,我看著自己剛才托過球的手,一抬頭,發現日向正在與我對視,臉上是比自己扣球得分後更寧靜一些,又更風暴一些的那種令人心悸的表情。
我伸出手,隔空與他碰拳。
他從天而降,腳踩人間,終於停止仰望王牌,成為貨真價實的直射日光。
他即將要去別的地方發光發熱。夏天結束了,夢想還沒有。我們即將離別,寂寞有,不捨有,期待也有。
嘴唇分開的時候我們的臉都是紅的。我別開眼睛,扯著日向的手往自己掌心裡面握。
還要再摸一下嗎?我彆扭地問。
哦,哦哦。日向紅著臉讓我牽著,笨蛋一樣點頭。
我們踩在同一條狹窄的平衡木上,筆直地前往同一個方向,這裡位置太小,能容下的人不多,只有專心致志的人能平穩前行。我握著日向的手,感到莫名的自信,前路受阻的夏天已經過去,總有一天我們還會一起。
只要一起,我們無敵。
by 匿名排民

留言